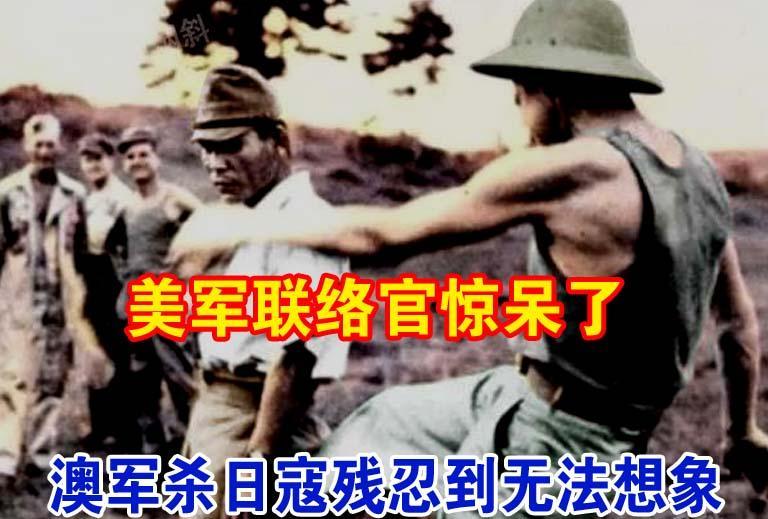[中国赞]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:我父亲是侵华日军,我从不吃中国菜,因为我不配,我也不生小孩,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。这样的血脉,必须要在我这一代终结。 (信源:百度百科——村上春树) 1994年,村上春树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,一场欢迎他的盛大宴会正在进行。宾主尽兴,气氛热烈,然而接下来的一幕,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 面对一桌子丰盛的中国菜,村上春树礼貌地拒绝了主人的热情,转而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罐罐头,自顾自地吃了起来。 这并非偶然的身体不适,而是一个他维持了一生的习惯。这个在外人看来近乎冒犯的举动背后,是他为自己建造的一座精神牢笼。而这座牢笼不止一个。 他不仅终生不吃中国菜,还做出了一个更决绝的选择——不要孩子,亲手终结自己的血脉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往事,能让一个人用如此极端的方式,来惩罚自己的人生? 这一切,都要从他的父亲说起。 在村上春树童年记忆里,父亲是个复杂的人。他有时对村上春树宠爱有加,但有时也会因为他的成绩而暴跳如雷。这种严厉比较在村上春树心里留下伤痕。然而,这点家庭内部创伤与他后来发现的真相相比,根本不值一提。 随着年龄增长,村上春树在图书馆史料中揭开父亲侵华日军的另一重身份。史书文字和照片击碎他心中父亲的形象,他无法将现在的父亲和双手沾满血液的那个人联系起来。父亲忏悔未让他释怀,反而激起痛苦与排斥,他无法将“加害者”身份与父亲画等号。 源自血脉的罪恶感如影随形,他认为自己的存在是父亲罪行的延续。最终,他裁决自己拒绝生育。 他曾公开表示,不像父母那代人对世界抱有信心,这并非悲观,而是主动切割。他要用“断后”这一激烈方式,将认定为耻辱的罪孽从家族血脉中铲除。 如果说不生育是为未来上的一道锁,那么不吃中国菜,就是他在当下为自己设置的一道壁垒。 这首先是公开姿态,他向世界宣告一辈子“没资格”尝中国菜以忏悔历史。此举赢得赞誉,也引作秀质疑。 更深层原因或许是生理性排斥,对他而言,中国菜不是食物,而是打开创伤记忆的钥匙,其复杂香气、蒸腾热气会让他联想到父亲过往与民族罪责。 这种心理暗示演变成生理抗拒,他路过中餐馆闻到味道就浑身不自在。因此,1994年宴会上他打开罐头的动作有双重含义:既是自我惩罚,也是保护自己精神的无奈之举。这道菜肴形成的鸿沟,映照出他因父辈罪行终生无法跨越的无形高墙。 可是,当我们将目光从他的个人行为转向他的文学作品时,会发现这场“赎罪”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和矛盾。 村上春树在小说中从不回避战争,也承认日本的罪行,但他常常巧妙地将责任引向抽象的“体制”和失控的“时代”,而不是像他父亲那样的具体执行者。 这种叙事策略,在某种程度上,倒像是一种高明的开脱。他终究是站在一个日本人的立场审视历史,他的痛苦更多源于“我的父亲是加害者”所带来的身份危机,而很难真正代入受害者的立场去感受那份苦难。 他曾将人比喻为雨滴,“我们不过是无数滴,落向宽阔大地的雨滴中,寂寂无名的一滴。”这句话充满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,但也暗含着一种将个体责任消解于庞大集体之中的暧昧。这不禁让人发问,如果每一滴雨都不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,那洪灾又是从何而来? 最终,村上春树用这种方式将自己与父辈的罪孽捆绑在一起,进行了一场漫长而孤独的仪式。他的故事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样本,它告诉我们,历史的创伤并不会自动愈合,反而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,在后代的灵魂深处刻下烙印。 他的挣扎与选择,无论是否完美,都以一种震撼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问题:当面对父辈的罪责时,后代究竟应该选择遗忘,还是该背负起不属于自己的十字架?而这其中的界限,又到底在哪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