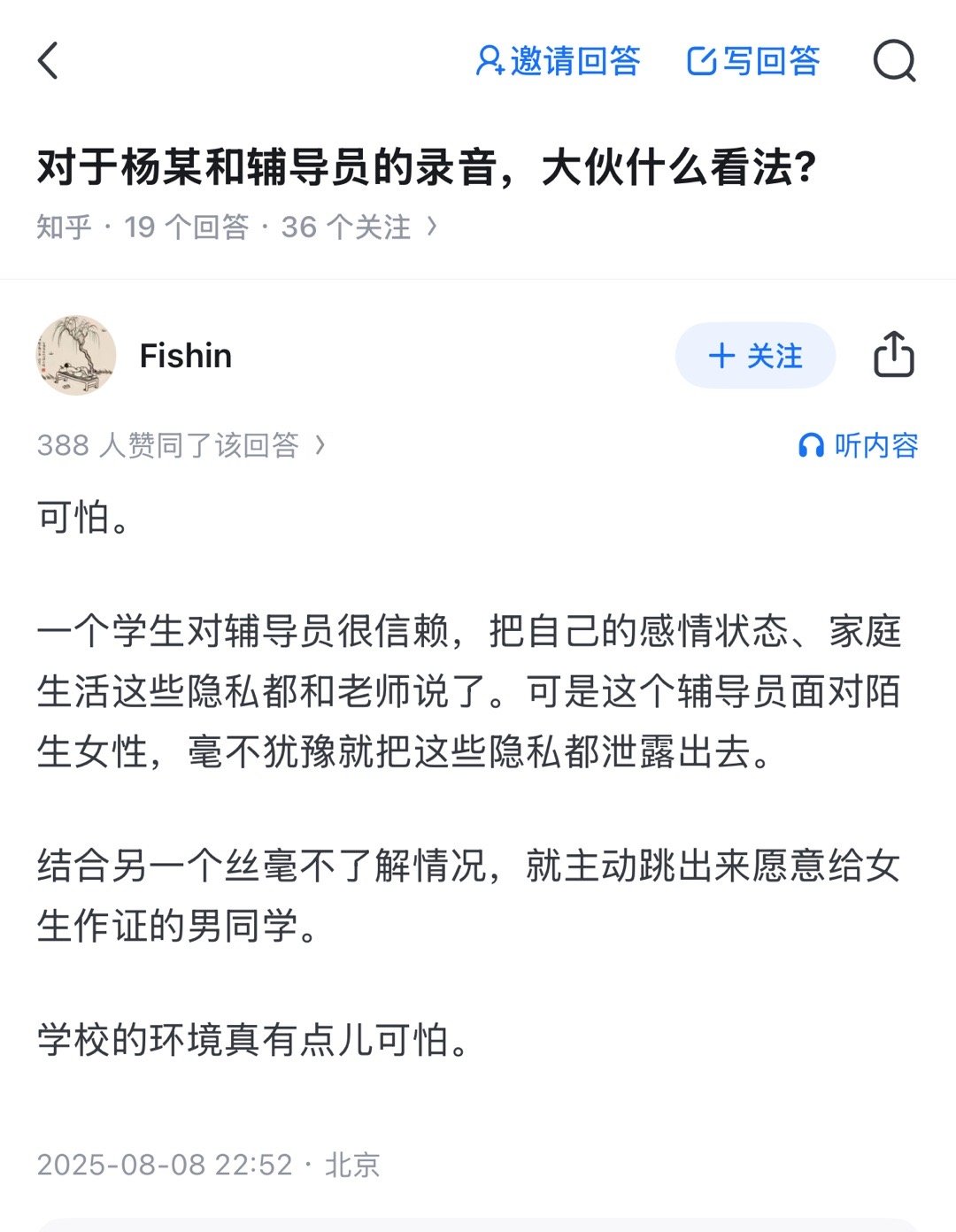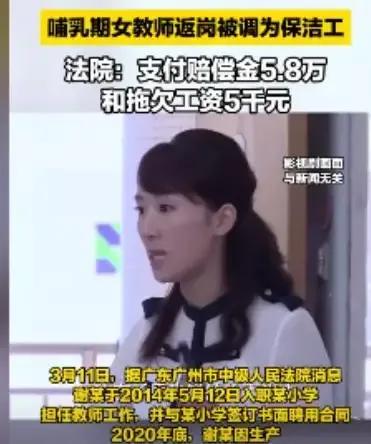“得不到就毁掉?”我国百年难遇的数学天才任伟,在美国学成后,果断拒绝了美国人开出的千万年薪,说什么都要回中国,他的带头也鼓舞了很多海外学子的归国热情,可就在他即将回国的前一天,却离奇死在了校园里。
2008年11月16日清晨,芝加哥大学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在校园里巡查时,发现洛克菲勒教堂南侧脚手架下有生命体倒下的声音。
赶过去一看是位年轻人,辞世的那个年轻人名叫任伟,是数学系博士生。就在人们还没缓过神,他的死亡被媒体报道为“自杀”或“坠楼”,而校园和警方的后续说明却既没有回应所有疑问,也没有说服所有人。 任伟不是那种只会写论文、把课堂演绎得枯燥生硬的“数学怪才”。同学眼中的他,能把复杂的数学概念讲给落后不少的同年级听懂,还常常组织课程讨论、数学沙龙,哪怕经费少、场地挤,也能搞得热热闹闹。 系里留学生里,任伟被认为是“那种开朗还爱讲段子的人”,和谁都能聊起来,特别是与后来想回中国发展的同学之间,他有种天然的引领感。 任伟从小在上海参加奥数拿了一等奖,中学跳级,用很快的速度就考上了国外名校。一路从科尔盖特大学打基础,再直接博士读到芝加哥大学。 按说这一路下来,等待他的战果应该是毕业典礼上的披袍、博士帽和家长欣慰的脸。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“前十页的人生计划表”,戛然而止在芝大那个浸冷晨露的教堂旁。 更怪的是任伟几乎要回国了,有人说他拒绝过美国提供的高薪保底、绿卡甚至股份承诺,坚持要回中国。 任伟说过自己学的东西要带回去,哪怕再迟一点,他都不会把根留在那边。围绕他的死亡,越听越像破纪录的谜团。 好几个同学反复提到:教堂晚上是关门的,怎么他就能出现在外面?监控“坏了”?值班记录“遗失”? 现场之后迅速被封锁,宿舍昨晚上还整整洁洁,第二天一开门,东西不见了:电脑、手稿、草稿本都不翼而飞。只留两张便条,有人代课、房租怎么付这种日常事,只像是他准备出门的安排,而不是告别。 警方很干练地声明还在调查,“无法排除自杀或他杀”等措辞显得既专业也冷静。学校发言人只说“我们在配合调查,正在联系他的家人”,之后就基本保持低调。 校方通报和官方流程走完之余,留给家属的却是太多“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”的不完整。 事情发展到这里,亲朋都炸了。有人两周前还和他吃饭聊计划,说感恩节去伦敦看朋友,怎么熬过一个夜,从筹划未来变成永别? 有同学痛快地说:他不可能像那样跳出去。更青天白日下留一个人站着,一句话都没留,对我们来说真的不可思议。父母从贵州赶来,又语言不通进不了局,说几句都得人代翻,站在芝加哥的寒风里哭他们唯一的儿子。 后来,这件事在网络上炸开了锅。留学生群体留言多是“天哪,他真的要回国,怎么就没了?”还有人干脆直呼“得不到就毁掉”,把它解读为某种警告,对人才的断绝可能是一种恐吓。 国内媒体转载的评论里,有人问:“留学生的安全谁来保障?”“关键科研不就是靠这些人吗?”国内一些高校、研究机构在这之后也开始提出保人安全、设立海外预警机制的建议,虽然靠这些没法填满一个坠楼的黑洞,但至少显得有点问题意识。 留学生群体看到这件事之后的心里是一种“如果换作我怎么办”的恐慌。天南地北,我们为了学术或梦想努力出国,也想安心回国,把学成带回去做事情,可一件悲剧就能把信心击得粉碎。 制度层面也开始思考:有没有什么机制是可以在身处海外的中国研究者们遇到突发事件时,被及时照顾?这不仅是一个个案,更是一个体制和制度的缺口。 最后说一句话:最尊重一个人的方式,不是把他的故事变成情绪的宣泄口,也不是把他变成某种政治符号,而是把所有能查到的事实整理透,把疑问摆上科学审视的桌面,等媒体验证、司法调查、学校回应都出来之后,再让真相公布,也让制度跟上。 任伟他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记忆的符号,他值得一个公平的答案,也让后来者知道:我们不会让这样的陷阱再吃下去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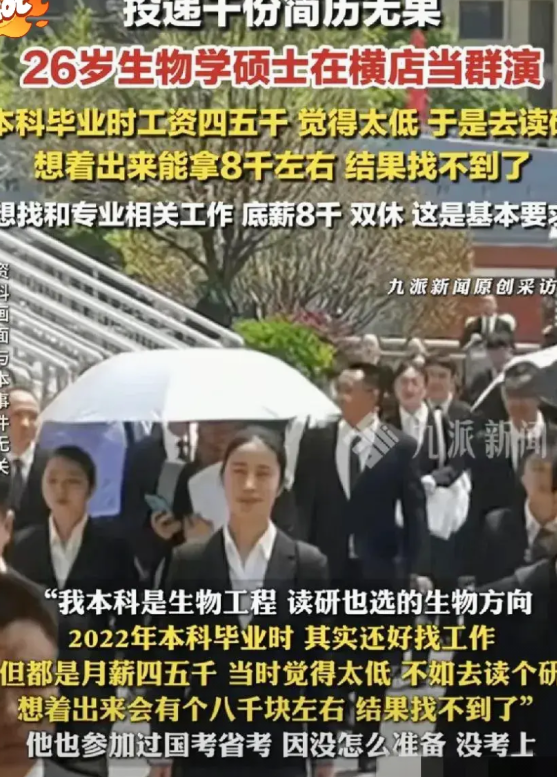



![高中同学要找我借钱结婚[汗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2204746890148179448.jpg?id=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