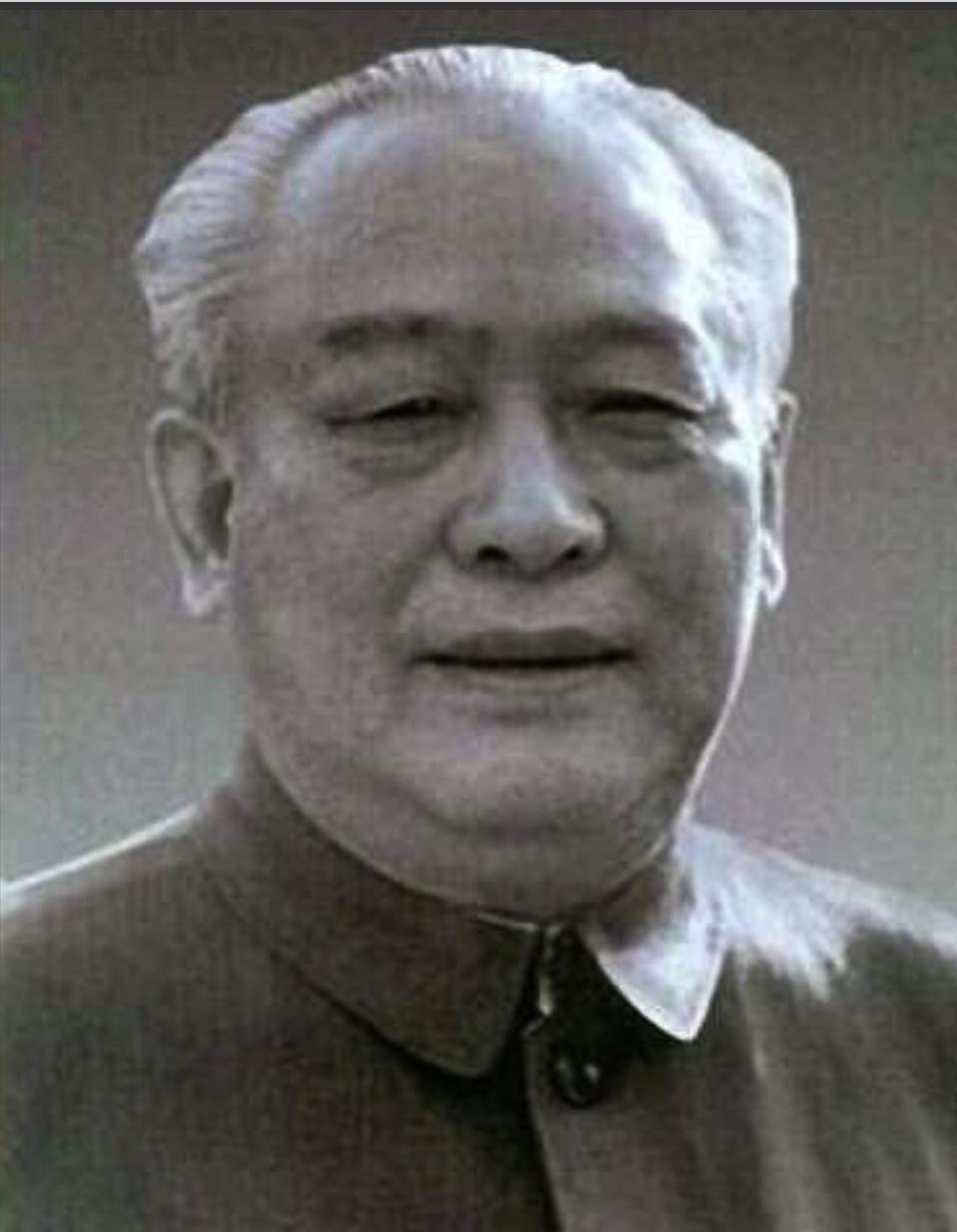1960年,石油部长余秋里为救大庆油田,找罗瑞卿要飞机运 5 吨焊条。罗瑞卿一听就火了:“你口气也太大了,真当空军是你家拉货的驴车?” 当时,石油更是我国工业的命根子。 1960 年 12 月 21 日深夜,北京东交民巷的石油工业部大楼,多数办公室都黑着灯,就余秋里的办公室还亮着。 这位少了条胳膊的部长,正盯着桌上的原油泄漏报告,眉头紧皱。报告上写着,每小时要漏掉 12.5 吨原油,这些油金贵着呢,看一眼都让他心里发紧。 突然,电话铃响了,在夜里特别刺耳。余秋里赶紧拿起听筒,电话那头是东北前线的人,声音急得发颤:“部长,出事了!输油管道又冻裂了三处,原油都快漫过三号泵站的警戒线了!” 余秋里 “腾” 地站起来,假肢在木地板上磕出 “噔” 的一声。他抓起军大衣就往外冲,一边跑一边喊:“备车,去总参谋部!” 警卫员赶紧跟上,追问他去哪。余秋里头也不回,语速快得很:“再晚半小时,大庆油田的高产井就得全停了,那损失扛不住!” 大庆油田的输油管道,在零下 40 度的雪地里铺着。1960 年这场奇冷,把苏联帮忙建的管道毛病全显出来了。焊接的地方在低温下脆得像玻璃,一碰就裂,原油一个劲往外冒。 更要命的是,修管道必需的特种焊条,因为中苏关系闹僵,已经断了三个月的货。 技术处长跑进来,声音带着点激动:“部长,沈阳机械厂找到库存了!” 可马上又蔫了:“就是铁路被暴风雪埋了,最快也得 15 天才能运到。” 余秋里一拳砸在地图上:“15 天?一天流 300 吨,半个月就是 4500 吨!这是要把新中国的工业血管给冻住啊!” 凌晨两点,总参谋部作战室里,顶灯照着罗瑞卿的脸,铁青铁青的。 他刚从福建前线回来,听完余秋里的请求,手指头重重地敲着桌子:“余秋里,你怎么想的?空军运输队是能随便动的?就 5 吨焊条,还要用战备飞机?” 接着,他突然拔高了声音:“知道伊尔 - 12 运输机多贵吗?能买 300 吨粮食!” 余秋里早猜到会挨训。他从口袋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纸,那是大庆工人用冻僵的手写的请战书,上面写着:“只要有焊条,就是用牙咬,我们也得把管道焊上!” 接着,他声音沉了下来:“总长前线的工人,已经三天没吃上热乎饭了。” 罗瑞卿眼神动了一下。他俩是老战友,他太了解余秋里了。 这人长征时丢了条胳膊,骨子里硬得很,不是逼到份上,绝不会开口求人。 可军队有纪律,战备物资不能乱动。他抓起电话打给贺龙:“老总,余秋里要抢我的飞机用!” 电话那头传来贺龙的大嗓门,带着笑:“让他抢!对了,多装两袋高粱米,别让石油工人饿着肚子干硬仗!” 12 月 23 日大清早,沈阳东塔机场的跑道上,两架伊尔 - 12 运输机的引擎 “嗡嗡” 响着。 机长李建国本来在修雷达,听完任务,愣了一会儿说:“把导航员换下来,这趟我亲自飞。” 地勤往货舱搬箱子时,见每个箱子都裹着厚棉被。原来是沈阳机械厂的工人,连夜把自家的被褥拆了,给焊条保暖。 飞机钻进暴风雪里,李建国的耳机里突然传来地面指挥的喊声:“03 号注意,前面有强气流!” 他把操纵杆握得死死的,看着仪表盘上乱晃的指针,想起三年前在朝鲜,也是开着这种飞机给上甘岭送弹药。 他对着对讲机喊:“同志们,下面流的不是原油,是新中国的血!这焊条,必须送到!” 飞机降落在萨尔图机场,底下的人全欢呼起来。工人们用冻裂的手拍着机身,手背上的口子还渗着血。机组成员下了飞机,都看呆了。 来接的人里,有的拄着木棍,有的裹着破草席,棉袄上全是补丁,看着就让人心酸。一个满脸胡茬的汉子敬了个礼,说:“首长,焊枪我们揣怀里焐了三天,就等焊条了!” 谁也没想到,那 20 袋高粱米到了前线,成了宝贝疙瘩。工人们一粒一粒地分,煮粥时先把米粒捞出来给伤员,剩下的米汤再分着喝。 焊工班长王铁人带着徒弟们轮着干活,困了就抓把雪往脸上抹,饿了就啃口冻得硬邦邦的高粱饼。 到第七天凌晨,最后一道焊缝焊完,王铁人 “咕咚” 一声坐在雪地里,焊帽里全是冰碴子,眼睫毛上也挂着冰珠,整个人累得直打晃。 12 月 30 日中午,余秋里站在修好的管道旁,寒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,他一点没感觉。阀门慢慢打开,一股深褐色的原油喷了出来。 余秋里蹲下身,用那只没残的胳膊接住第一滴油,滚烫的油珠在他粗糙的手掌上,慢慢凝成了琥珀色的小球。 “部长,出油了!出油了!” 周围的人都喊了起来,声音里全是激动。 余秋里抬头往远处看,油田的井架一个挨着一个,立在雪地里。他心里清楚,这场仗打赢了,不光保住了每天 300 吨原油,更保住了新中国工业的盼头。 四十年后,国家博物馆里还放着那截带补丁的输油管道。余秋里和罗瑞卿吵的那一架,表面是争着用飞机,实际上,那是新中国在难日子里,拼命往前闯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