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当兵的时候已经是21岁了,也就是当兵超龄前最后一年到的部队。本来到部队之前怀揣
孟嘉佑阿
2025-07-24 10:55:52
我当兵的时候已经是21岁了,也就是当兵超龄前最后一年到的部队。本来到部队之前怀揣着考军校的念头参军的,在临入伍之前,我把高中课本都翻了出来,用塑料布包好塞进了行囊。母亲往我背包里塞了二十个煮鸡蛋,父亲站在门口抽着烟,只说了一句:"到了部队,别给老张家丢人。"
新兵连的第一天,班长让我们挨个报年龄。当我说出"21岁"时,全班都笑了——这群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管我叫"老同志"。班长拍拍我的肩膀:"年纪大点好,懂事。"可这份"懂事"在新兵训练里没给我带来任何优势。第一次三公里跑,我落在最后,肺里像塞了团棉花;单杠训练时,比我小两岁的李强轻松拉了八个,我吊在杠上像条风干的咸鱼。
熄灯后,我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数学课本。同班的王浩探头问:"老张,你真要考军校啊?"我没说话,把写满公式的笔记本塞到枕头底下。第二天早晨,班长在检查内务时发现了那个笔记本,他翻了几页,什么也没说。但从此以后,每次体能训练结束,他都会多留我在操场跑两圈:"想考学?先过了体能这关。"
第一次摸底考试,我的文化课成绩排全连第三。指导员找我谈话时,我正在医务室往脚上抹药——每天的加练让我的脚底磨出了血泡。"有想法是好事,"指导员递给我一盒膏药,"但部队不需要书呆子。"那天晚上,我把课本锁进了储物柜,开始跟着班长加练战术动作。匍匐前进时,手肘在砂石地上磨出血痕;练据枪时,往枪管上挂水壶,一挂就是半小时。
春节前,连里组织军事科目比武。我报名参加了战术综合考核,在穿越铁丝网时,右腿被划开一道口子。血顺着迷彩裤往下流,但我没停——21岁的"老同志"咬着牙第一个冲过终点。团长亲自给我颁奖时问:"听说你想考学?"我立正回答:"报告首长,先当好兵再想别的!"团长笑了,转头对政委说:"这样的兵,部队需要。"
第二年开春,连里推荐士兵考学名单。当班长念到我的名字时,我正站在队列里擦枪。指导员说:"给你三个月准备时间,但日常训练不能落下。"于是每天凌晨四点,学习室的灯总会准时亮起。五点半出操前,我已经背完三十个英语单词;午休时间,别人睡觉我刷题;晚上熄灯后,打着手电在被窝里推导物理公式。有次夜里查岗,连长看见学习室亮着灯,推门发现我趴在桌上睡着了,面前摊开的模拟卷上还沾着口水。他没叫醒我,只是轻轻关了灯。
考试前一周,我发起了高烧。卫生员量完体温说39度2,要给我开病假条。我把条子塞进口袋,照样跟着队伍去靶场。打靶时,准星在视线里晃成重影,但我还是打出了48环的成绩——比平时少了7环,但足够优秀。团长知道后,派司机连夜送我去军区医院。躺在病床上输液时,我看着窗外站岗的哨兵,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军人的坚持。
军校考试那天,全连都在大门口送我。班长往我兜里塞了块巧克力:"别紧张,就当平常测验。"走进考场时,我的迷彩服右臂上还别着"优秀射手"的徽章。试卷发下来,发现最后一道大题居然是战术想定作业——这半年的训练经历让我的答案比教科书还生动。
放榜那天,我正在炊事班帮厨。指导员举着电报冲进来:"好小子,全军区第七!"炒菜的大勺咣当掉在地上,我抹了把脸,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。晚上全连加餐,团长特意过来敬酒——以茶代酒:"到了军校,别忘了你是从咱们钢铁七连走出去的!"
离队前夜,我收拾行囊时发现那本沾满汗渍的高中课本。班长推门进来,递给我一个崭新的战术背包:"拿着,装你的军校教材用。"月光透过窗户,照在我们俩的肩章上——他的是一道粗拐,我的还是光板,但我们都清楚,明天太阳升起时,一切都会不一样。
现在每次路过新兵训练场,我总会多看两眼那些气喘吁吁的年轻人。有个21岁的"大龄新兵"正咬着牙做引体向上,阳光照在他涨红的脸上,像极了当年的自己。背包里露出课本的一角,那塑料封皮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1
阅读:1033
![长春航空开放日上的歼-20机头细节特写[墨镜]图一是DAS系统窗口图二是上一代E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0730407768648478762.jpg?id=0)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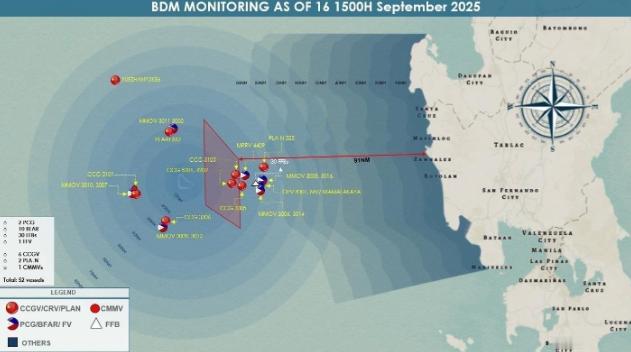

刘瑞云
你他妈真能编,难为你编这么多字
Tomorrow
考核打靶100米胸环靶,5发子弹,45环是优秀,全部命中靶心是50环,你打了48环,比平时少了7环~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