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寺庙,这么多和尚吃饭,他们不工作,不种粮,不服兵役。如果哪一天没有了香火供奉,他们没有技术,没有体力,他们吃什么? 一直以来,大多数人对寺庙的印象都是光鲜和肃穆的:香火缭绕,钟声悠远,和尚们无需耕种、不需赚钱,却能每日温饱。 这种由传统供养支撑的寺庙经济,在我们印象中几乎从来没有动摇过,但真的是这样吗?哪个系统可以永远运行而无需回应现实? 很多人不知道的现实是,寺庙经济早就被时代卷入了洪流,尤其是近几年,香客骤减、旅游降温、寺庙经营面临“断粮”风险的寺庙,远不止一座。 在没有供养的日子里,曾经那些以“弘法利生”为职责的僧人,不得不开始有了不同的思路,清修不再是唯一的日课,想办法生存,成为必要的现实。 香火从来不是稳定收入,最多的几年能给寺庙带来一些宽松,但香火依赖于人心,人一走,香也灭了。 2019年前,寺里每天能接待数千游客,门票加祈福收入撑起了寺庙运转,厨师、保安、维修工、管理人员全靠这笔钱维持。 现在,看守山门的保安也兼任了电工,断电了自己修,僧人也开始学会用Excel做法会统计。 如果还觉得寺庙还靠着民间布施和朝拜者供养来“白吃白喝”,那就太过简单了。 现代寺庙已经彻底告别了古代“靠地吃饭”的格局,上千年来,中国寺庙经历了从“乞食”自在到“自食其力”的蜕变。 唐代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不是修辞,是生存,那时的和尚分明就是佛院里的农夫、劳动者。一边修禅,一边种地。 到了宋元,土地渐多,布施也畅,寺庙有时甚至拥有规模庞大的寺产,历史上,北方大寺动辄拥有三千亩地,可自给自足。 但土地改革之后,土地进入国家统一管理系统,寺庙不再拥有固定资产,改革开放后,旅游变成寺庙的主要生计来源,这就意味着,游客减少,他们的饭碗就有问题。 2025年6月,西藏昌都,僧人索朗参加了地区政府组织的水电维修培训班。 这个29岁的年轻人,从小在庙里长大,连手机都不曾熟练使用,但一个夏天后,他能够检查电路跳闸、重新布管配件。 这种现实主义正在许多现代僧侣之间蔓延,传统的诵经打坐之余,越来越多的年轻僧人开始学习法律、英语、计算机、心理咨询——他们试图重新定义“佛法”的现代边界。 2024年底,山东某佛学院展开互联网课程开发计划,邀请高校教授与科技公司共建“禅修心智App项目”。 主讲的教育长说:“如果现在的人会在晚上十一点打开抖音学佛,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手机上打开禅堂?” 这时候有人要问了:可这不是违背了佛教的“出世”之义吗? 现代很多寺庙确实恍若公司,进去看到的是收银台、旅游路线图、义工招募表和微信扫码付款码。 僧人穿得整整齐齐说欢迎光临,还帮你引导拍照角度,佛像巍峨,但文字简介简化成了三行英语+一张QR码。 怎么平衡人间烟火与教义精神,这不是新问题,佛教从未在象牙塔里长大,过去千年里,它在战乱中靠布施生存,在朝代更替中与权贵周旋,它从没真的“自由”。 真正的核心矛盾,不在于和尚有没有手艺,而在于这个系统是否还能维持对精神的追求本质,换句话说,现代和尚的问题不是吃饭,而是“吃饭之后干什么”。 这就是现在寺庙生存的微妙状态:它已经无法靠纯粹的香火支撑,但又不能完全世俗化。 一旦完全变成营利单位,僧人的角色就变成了经营者,对佛教来说则是极大的空心化风险。 商业化是一柄刀,没有收入维持不了修行空间,有了收入可能忘了修行本意。 宗教的核心,是信仰的深度,而深度从不靠包装和流量来保证,它需要一种超越效率的纯粹空间,可是在现代社会,没有经济基础的空间是活不下去的。 某种意义上说,“和尚吃什么”这个问题,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提问:当传统宗教面对现代社会的逻辑时,它还能不能继续存在? 从内容上看,现代僧侣确实已经不再是对现实视而不见的群体,他们开始进工信局学习技能,开始掌握公众号和社群管理,甚至开始做文创。 有人讽刺说“和和尚聊佛法不如聊运营”。 但也请注意,这种表面的工具化背后,还有不少僧人试图坚持一种不被污染的核心,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,但“尝试守住”这三个字已经足够珍贵。 没有人天生该替他人说法,僧人不是供养下的神祇,也不是经济洪流中的最后庇护者,他们也吃饭,也思考,也做选择。 清修之道,不是放弃世界,而是与世界保持一种必要的距离,维生,是底线;弘法,是目标。 现实从来没有改变佛法的初衷,只是逼着它换一种语言,一种方式继续存在。 假如哪一天真没有了香火,没有了功德箱、门票和祈福卡,那些修道人也依旧会活下去。 他们可能只剩下一盏灯,一本经书,一个平坐的蒲团,在破败、大殿屋檐暗漏的角落,他们继续合十,这才是最真实的佛门。 不是和尚吃什么,而是我们以什么视角看佛门的存在,需要他们,是社会;允许他们,是制度;能否真正理解他们,是文化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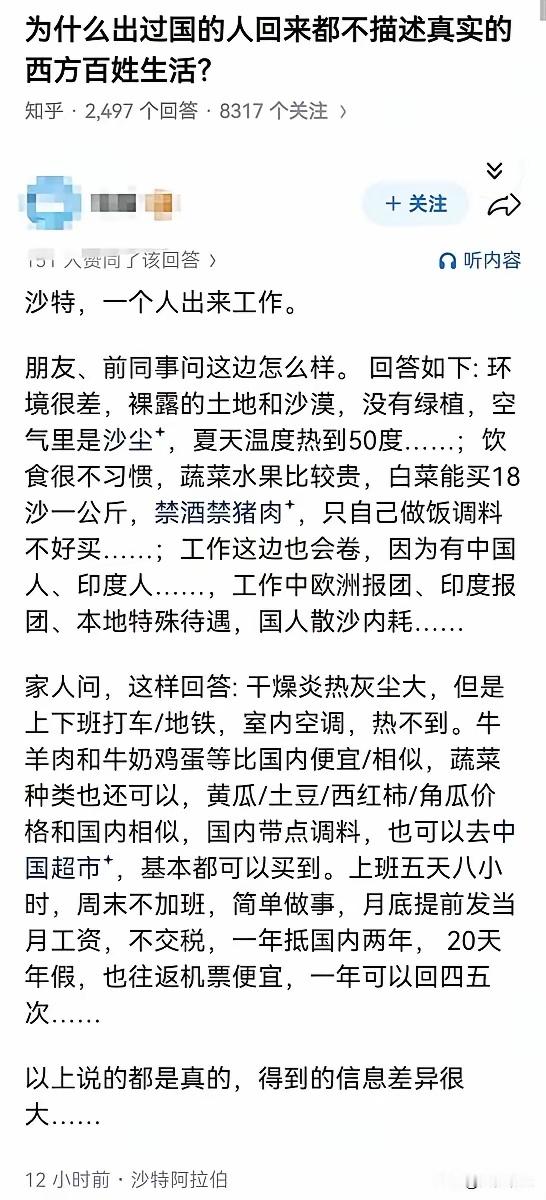



舒逸飞
有编制,准公务员待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