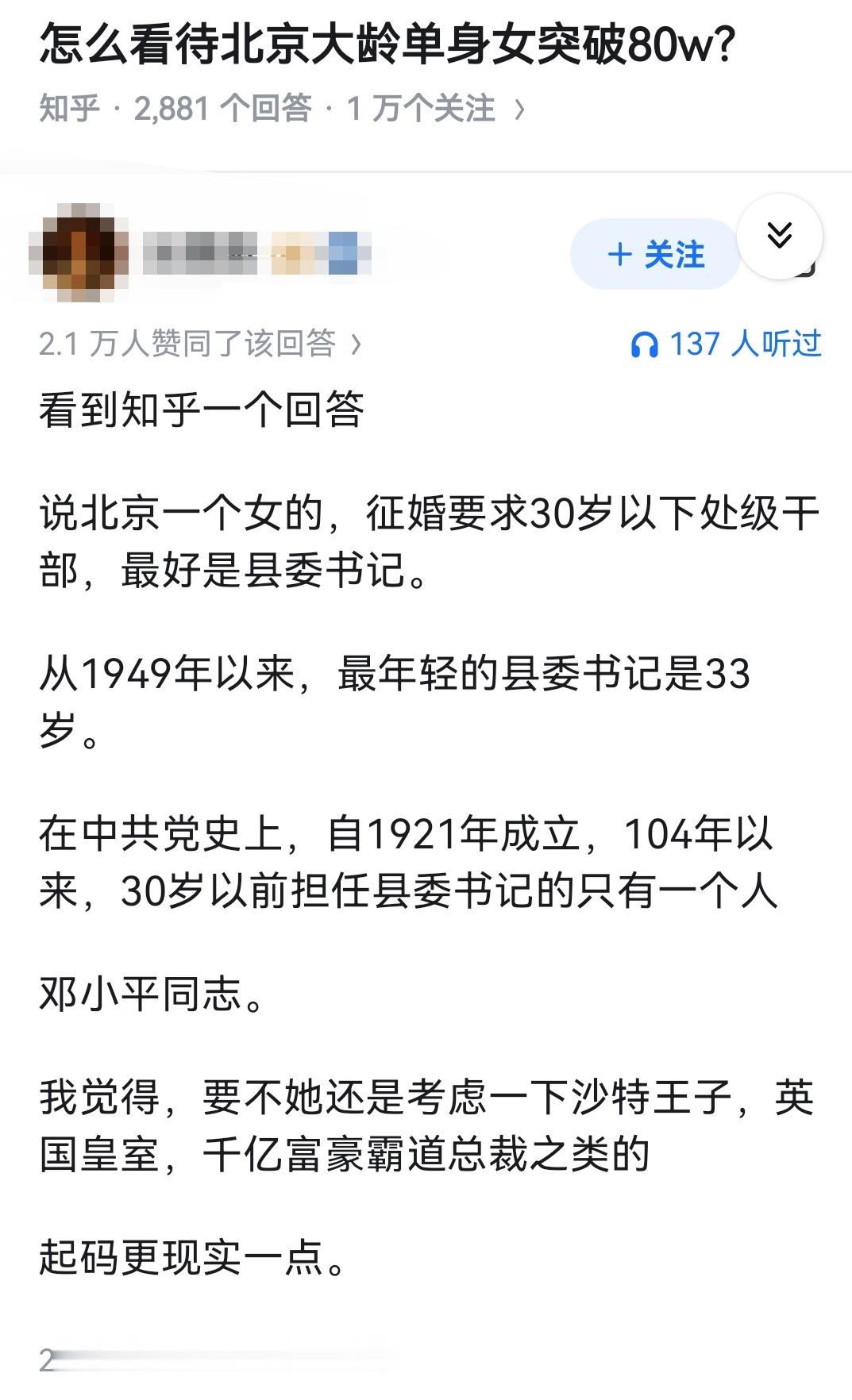我们村一个人,在北京当兵。从离家当兵开始,就是结婚回了一次家。跟家里任何人不来往,包括兄弟姐妹,从来不在亲戚身上花一分钱。村里人都叫他老陈,今年快五十了。 快五十的老陈,在村里故事里还是那个十七岁的背影——冬天的风掀起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褂,打补丁的帆布包拍着后背,里面两件旧衣裳裹着本新华字典。村东头二柱妈看着他往村口走,跟搓玉米的婶子们说:“这娃眼神里有股狠劲,怕是要把根从咱这土疙瘩里拔了去。”那时没人当真,只当山里娃头回见火车道,心飞野了。 谁能想到,这“野”心一扎就是二十年。头半年,他爹扛着锄头路过老槐树,总要站一会儿。烟袋锅在树疙瘩上磕三下,望着通往镇上的土路,烟圈裹着晨雾飘到树杈,惊飞几只麻雀,才叹口气往回走——闷葫芦老爹唯一的念想,都在那口烟里。他妈夜里攥着他旧布鞋抹泪:“说好了每月写信,这都仨月了,连个邮戳印儿都没见。” 第五个月,信来了。绿格子纸,字歪歪扭扭像爬着的蚂蚱:“爹,娘,训练不累,吃的饱,勿念。陈军。”他妈数着字哭:“把‘建军’改成‘军’,是嫌家里名土?”可这信写了两年,突然就断了。邮局翻出三封发霉的信,才知道王大爷眼神花,把“陈军”认成“陈建军”,堆在角落沾了潮。最后那封信里有张照片:天安门广场前,他穿军装笑,胳膊上缠着纱布,脸黑得像刚从煤窑里出来。他妈摸着纱布印子,眼泪把照片泡出了褶子:“受伤了都瞒着,这犟脾气随谁?” 村里早炸开了锅。二柱妈拍着大腿喊:“我早说他混忘了本!”有人压低声音:“莫不是在部队犯了错?”直到二十五岁那年冬天,绿色吉普车停在村口碾盘上,他穿皮夹克,头发梳得锃亮,身后跟着穿红棉袄的北京姑娘。先去二柱家,塞糖给二柱妈:“婶,当年谢谢您照看我爹妈。”二柱妈手缩在围裙里,脸比冻红的萝卜还红。 回家杀了鸡,他妈拉他进里屋:“转业回县城吧,找个安稳活儿。”他没吭声。第二天留五百块钱,他爹抓起钱摔地上:“我不要你的钱,要你回来!”吉普车“突突”开走时,扬起的黄土迷了全村人的眼。这一走,就成了诀别。他爹妈走时,都是弟弟操办丧事。出殡那天,村口停着辆黑色小轿车,没人敢认。 现在村里年轻人听老辈说这故事,总问:“他咋不回来?”他妹妹快四十了,头发白了一半,赶集时跟我说:“前几年他打电话,问家里咋样。我说都好,让他回来看看。他就‘嗯’了一声,挂了。”或许,有些沉默不是心硬——就像他爹对着老槐树抽烟,烟雾里藏着没说出口的牵挂;就像他胳膊上的纱布,藏着没写进信里的疼。 快五十的人了,村口老槐树还在,只是当年蓝布褂上那颗他妈连夜缝的扣子,怕是早磨没了。北京的夜里,他会不会偶尔想起那个冬天?一步三回头的少年,帆布包里的新华字典,夹着家里最后一点温度。
我们村一个人,在北京当兵。从离家当兵开始,就是结婚回了一次家。跟家里任何人不来往
好小鱼
2025-12-17 19:50:29
0
阅读:6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