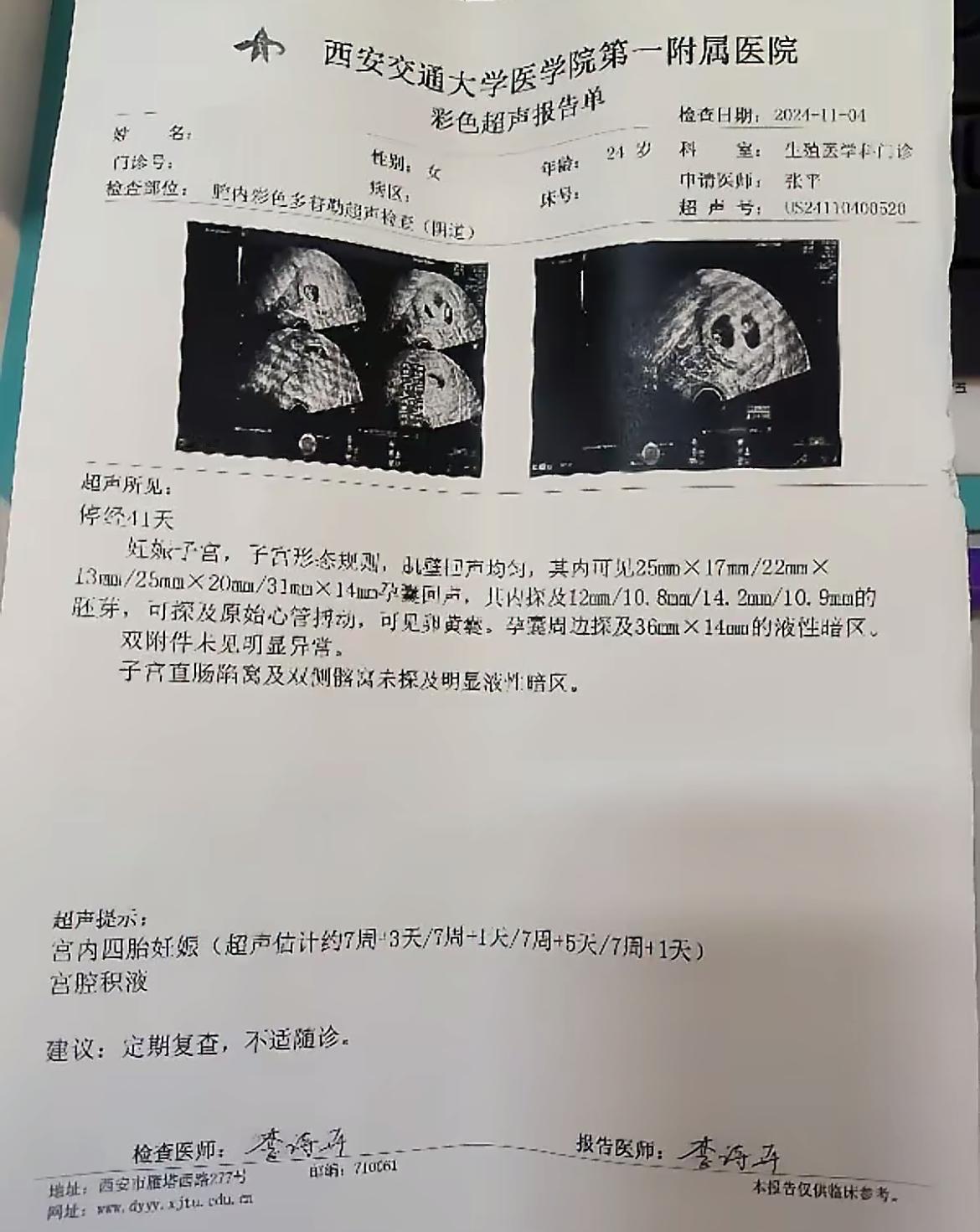上海某老式弄堂的清晨,总见一个戴老花镜的老人提着菜篮穿过青砖拱门。 邻居们只知道他姓徐,退休前在报社工作,却少有人提起他曾是上世纪60年代上海滩炙手可热的"笔杆子",徐景贤。 这条不足百米的弄堂,藏着太多被时光磨平的故事。 1981年保外就医后,徐景贤几乎是逃进了这里。 彼时城市正忙着改革开放,没人在意这个总穿蓝色中山装的男人,曾在《解放日报》的油墨香里搅动风云。 居委会登记册上,他的职业栏填着"无业",却在床头柜抽屉锁着三枚褪色的工作证。 在这条始建于民国的弄堂里,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。 他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,用煤炉烧水泡茶,报纸要从第一版读到中缝广告。 有次邻居撞见他在路灯下抄《古文观止》,问起时只笑笑说"老年痴呆,练字防忘事"。 两个女儿的婚事,成了徐景贤晚年最犯愁的事。 大女儿谈的对象是工程师,对方父母听说未来岳父身份,连夜托人退了亲。 那段时间,弄堂里总飘着中药味,他急得犯了严重的胃溃疡。 后来小女儿嫁给了菜场卖鱼的个体户,婚礼当天他躲在房间没出门,只让妻子送去一个红布包,里面是积攒多年的稿费存折。 1995年外孙出生那天,徐景贤在弄堂口站了整整两小时。 孩子满月时,他把珍藏的《鲁迅全集》包上牛皮纸,扉页用铅笔写着"送给小远:读书先学做人"。 从此弄堂里多了道风景:老人牵着穿开裆裤的娃娃,在梧桐树影里一句句教《唐诗三百首》。 2003年冬天,他开始整理旧物。 泛黄的《解放日报》合订本码满了阳台,老花镜度数换了三次,钢笔水用掉十二瓶。 2007年清明前,弄堂石库门的铜环被摩挲得发亮。 徐景贤走的那天,雨下得很大,送葬队伍里没有花圈,只有两个女儿捧着的骨灰盒,盖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,那是他生前常穿的中山装布料。 回忆录的最后一页停在1981年的春天,钢笔字写着"保外就医通知书送达时,窗台上的文竹刚抽出新芽"。 如今那盆文竹在小女儿家的阳台上长得茂密,而弄堂里的老邻居们偶尔还会提起:"老徐家的酱油鸡,味道比杏花楼还地道。 "在晨光里教外孙写字的身影,或许才是这个曾搅动风云的老人,留给世界最真实的模样。


![你们一堆成年人欺负我….[笑着哭]近日上海,高铁上发生了这样的一幕,一个宝妈带着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7583722748837147198.jpg?id=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