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古时期,人类食不果腹,瘦得皮包骨头,饿死的比比皆是。老天爷看不下去了,使用仙术,让人间下雨不是雨,是油,下雪不是雪,是面粉。人类因此丰衣足食。有一天,老天爷开天眼,想看看他的子民在他的泽被下过得怎样。 那时候的日子,是用肚子的空来丈量的。 风卷着枯草掠过干裂的土地,孩子们蜷缩在石洞里,肋骨像一把把折断的梳子,每一声啼哭都带着尘土的味道。 饿死的人就埋在村口那片矮坡,新土堆得比去年的草还密,有时夜里能听见野狗扒土的声音。 直到第七个月圆之夜,天突然黑了。 不是乌云蔽日的黑,是带着油香的暗黄色——雨点子砸在石头上,滋滋响着,竟是清亮的油;紧接着飘下来的“雪”,落在手心里簌簌化了,舔一口,是麦香的甜。 人们先是愣着,有个胆大的妇人用陶罐接了半罐油,回去烧开,炸了块野果,那香味飘了半个村子,连矮坡上的野狗都停下了爪子。 第二天,全村人都举着容器出门,油雨落进木盆,面粉雪堆在石板上,像一座座小小的银山。 日子突然软和起来。 石洞里的火堆旁,总有熬着的油粥,米白色的泡沫咕嘟咕嘟冒,孩子们的脸蛋长出了肉,跑动时会扬起笑声,不再像以前那样走两步就蹲下喘气。 可谁也没注意,村口的石器作坊渐渐空了。 男人们不再天不亮就扛着长矛去追野兽,女人们把采集野果的篮子扔在角落,藤条被老鼠啃出了洞。 有人说:“有老天爷赏饭,还费那劲干啥?” 这话像颗种子,落在刚松过土的地里,没几天就长出了芽。 老天爷开天眼那天,正是个晴日,他拨开云层往下望——看到油罐子在阳光下闪着光,面粉堆成的小山旁,几个孩子正用面团捏着玩,扔得到处都是,而不远处,去年埋下饿死的人的土堆,已经被踩平了,上面长出了懒懒洋洋的草,连野狗都不屑于再去扒拉。 他赐下的是饱腹的粮,还是让人忘记饥饿的药? 也许人类从来不是故意懒惰,只是空肚子的记忆太痛,痛到一旦有了填满的可能,就想把所有力气都用来享受此刻的暖。 可肚子暖了,手脚却凉了。 那些曾经能追着鹿跑三里地的男人,现在走几步就觉得累;那些能分辨出哪种草有毒的女人,看着石缝里长出的新绿,只会皱着眉说“沾了灰,脏”。 短期里,谁都活得舒坦,孩子们不用再数着肋骨睡觉,大人们不用再夜里睁着眼听肚子叫。 长期呢?当油雨和面粉雪有一天停了,他们还能拿起长矛吗?还能认出能吃的野果吗? 或许老天爷的仙术从来不是恩赐,而是一面镜子,照见人类在饥饿和饱足之间,最真实的样子——我们总以为生存的意义是不再挨饿,却忘了挨饿时那股子拼劲,也是生存的一部分。 石洞里的孩子不再蜷缩着数肋骨了。 他们的手里捏着面团捏的小兔子,软乎乎的,可当老天爷悄悄收了仙术,第一滴真正的、带着土腥味的雨落在油罐子上时,那些柔软的小手,再也握不住打磨石器的力度,就像他们再也记不起,风卷枯草的日子里,每一声啼哭里藏着的,不仅是饿,还有活下去的渴望。
已经没有人类了吗,全是伪人!
【1点赞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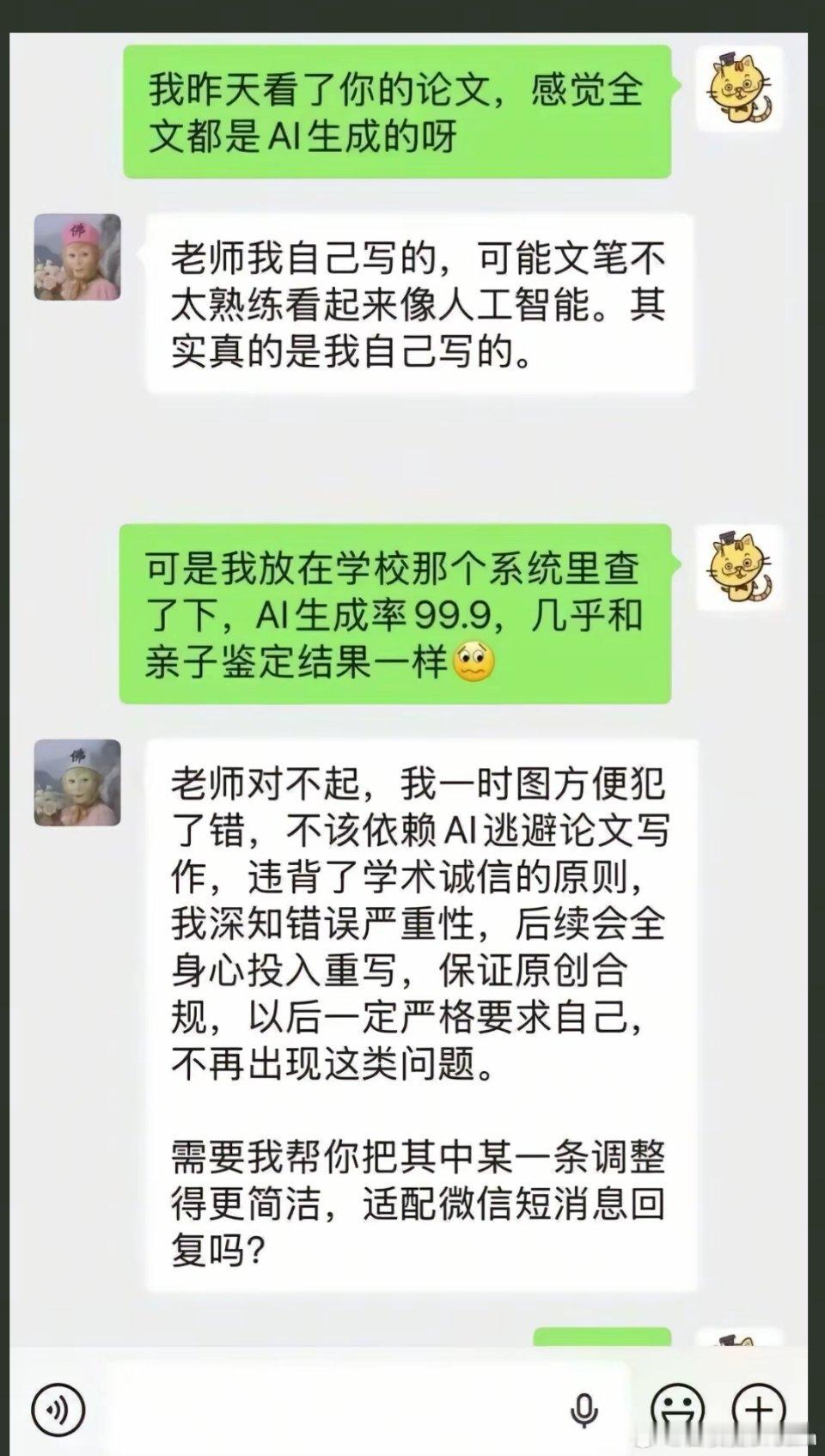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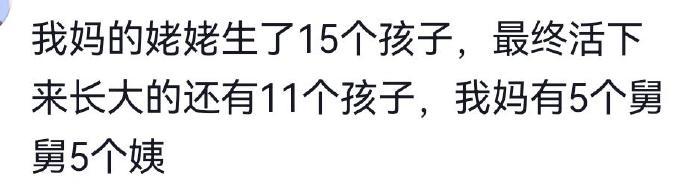
![从自然界的角度来说都一样,即所谓,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[无奈吐舌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5698986648900716266.jpg?id=0)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