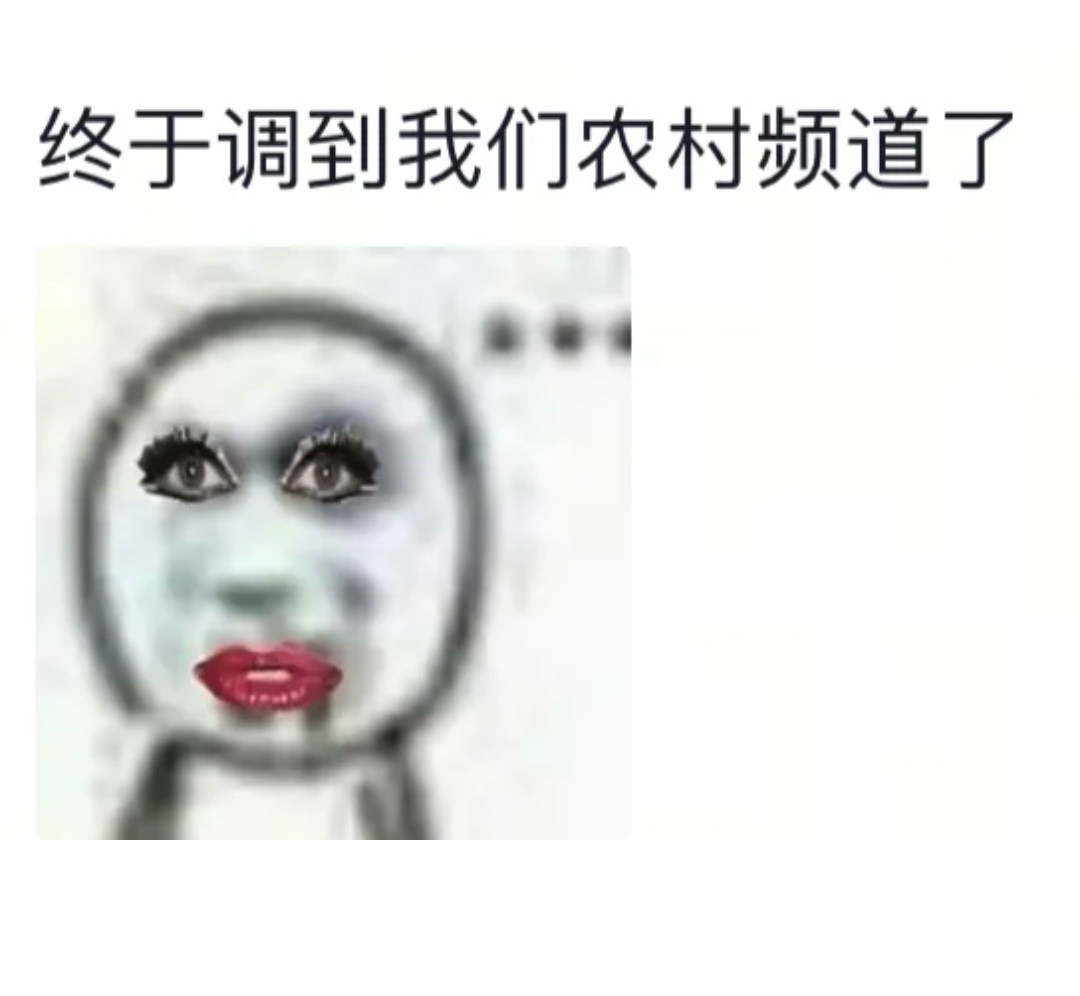我们村上有一个男生娶了一个老婆很漂亮,但是生了孩子之后这个男的就出门打工了,这个女孩子就在家带孩子,然后公公婆婆在家里要种地又养的有羊没时间照顾小孩,然后那个女孩子自己照顾着,但是手里没有钱买新衣服那个男的出门打工,每次打电话都说工资要等工程结束才结,让她先跟邻居借借,等他回来就还。 她蹲在灶台边揉面时,总能听见羊圈里老母羊的叫声——那是公婆唯一顾得上的活物,而她怀里的孩子正啃着手指,袖口露出的手腕细得像根晒蔫的葱。 衣兜里摸不出半张整钞,孩子的裤腿短了,她就把去年的棉袄拆开,把里子布剪下来接在裤脚,针脚歪歪扭扭,深浅不一的蓝布像块拼贴的天空。自己那件结婚时的红外套,领口洗得泛了白,风一吹就贴在背上,像片缩水的叶子。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总带着电流杂音:“等工程验收了就有钱。”她对着听筒嗯了一声,瞥见窗台上的酱油瓶空了三天,瓶底结着层黑褐色的垢——邻居家的酱油上次借过,这次实在张不开嘴。 后来村口扬起尘土,男人拖着蛇皮袋回来了。她正在给孩子缝补开胶的鞋子,针还扎在指头上,血珠渗出来,她却笑了——以为蛇皮袋里装着给孩子的新鞋。 蛇皮袋被拉开,滚出来的不是奶粉和布料,是半袋换下来的工装,还有个亮闪闪的新手机。第二天一早,老母羊不见了,羊圈的木桩上还拴着半截断绳,男人蹲在门槛上发朋友圈:“工地上的兄弟,我还行!”配着张戴着安全帽的照片,背景是她从没见过的高楼。 孩子光着脚在院子里跑,小脚丫踩在泥坑里,印出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。她突然想起自己八岁那年,也是这样光着脚追蝴蝶,跑过晒谷场时被碎玻璃划破脚心,血滴在麦秸上,像开出的小红花——那时候没人管,现在她却连双胶鞋都给孩子买不起。 那天夜里,她翻出压在箱底的结婚照。照片上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,她的红外套还很鲜艳。背面有行铅笔字:“等我赚够钱,带你去看海。”她盯着那行字,突然笑出声,眼泪砸在照片上,晕开了墨迹。她把照片撕成碎片,扔进灶膛,火苗舔舐着纸片,像在吞掉一个过期的承诺。 第二天她背着孩子去镇上,先把孩子送进托儿所,交了预支的学费——那是她偷偷攒的鸡蛋钱。然后去县城的商场,找到夜班保洁的活,凌晨三点的路灯下,她提着扫帚扫地,脚底磨出的泡破了,黏在袜子上,走一步疼一下,可手里攥着的工资单上,“2800元”的数字像团火,暖得她手指发颤。 三个月后男人突然回来,身后跟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,说要开饭店。他看见她时愣了愣:“你怎么瘦脱相了?”她正给窗台上的多肉浇水,水珠顺着叶片滚下来,滴在水泥地上:“干活干的。” “孩子呢?”他往屋里瞅。 “托儿所。”她把水壶放在窗台上,发出轻响。 他皱起眉:“你一个人带孩子怎么不早说?” 她抬起头,眼神静得像村口的老井:“我说的时候,你在听吗?” 他张了张嘴,没说出话。她转身进了里屋,背影挺得笔直,像田埂上那棵被雷劈过还活着的老榆树。 再后来,村头开了家小店,招牌是块旧木板,写着“破布也开花”。墙上挂着布艺娃娃、布包,每个物件的角落都缝着线头,其中一个娃娃的肚子上绣着行小字:“别等他回头,先学会自己走。” 评论区吵翻了天。 有人说她心狠,孩子不能没有爹;有人说她清醒,总比耗死在泥坑里强。 可我想问——那个在灶台边缝补衣服时,连针都捏不稳的女人;那个在凌晨三点的路灯下,数着工资单掉眼泪的女人;那个把结婚照扔进灶膛时,手都在抖的女人——她到底是狠,还是终于活明白了? 你们说,到底谁更可怜?是那个守着空承诺不肯走的人,还是那个终于敢转身的人? 别吵了,来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
我们村上有一个男生娶了一个老婆很漂亮,但是生了孩子之后这个男的就出门打工了,这个
青雪饼干
2025-12-08 18:49:47
0
阅读:4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