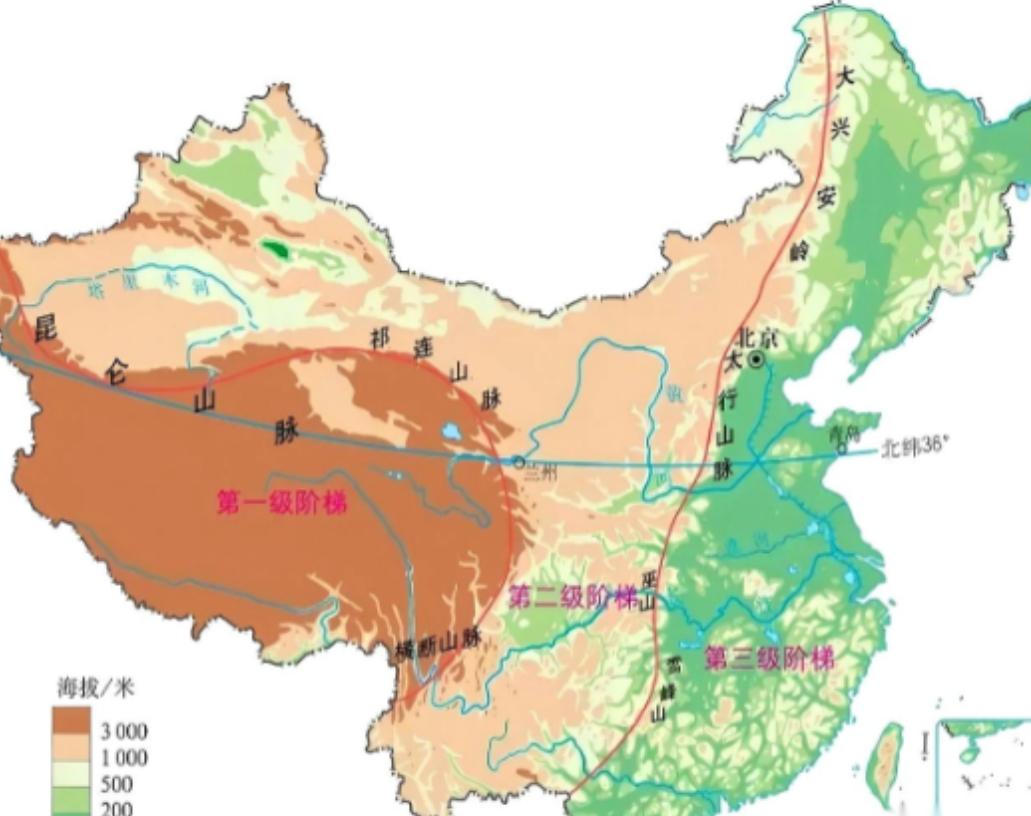为何同根同源的华人,对中华情感却如此不同? 世界上有两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,一个与中国血脉相连,甚至甘愿付出生命,另一个却嫌弃中国,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血脉。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街头,华文小学的校门口挂着褪色的木牌,上面“忠孝廉耻”四个毛笔字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,却依然能看出笔锋里的力道。 这里的华人只占全国人口的23%,却倔强地办起了1284所华文小学,课本里的唐诗宋词和马来西亚的地理知识并排躺着。 1941年的槟城码头,华人商贩陈阿水把刚收到的货款塞进竹筒,连同仓库里最后一箱奎宁丸一起搬上货船。 那艘挂着挪威国旗的货船最终没能抵达重庆——在马六甲海峡被日军潜艇击中时,船员里有12个华人,无一生还。 整个抗战期间,马来西亚华人捐出的54亿法币,相当于当时中国军费的三分之一;而日军为报复这场“跨海支援”,在槟城、吉隆坡等地展开的屠杀,让10万华人永远留在了那片橡胶林里。 转过马六甲海峡,新加坡滨海湾的写字楼里,年轻的律师林明轩正在修改一份合同。 客户用中文发来需求,他却习惯性地用英文回复,末尾加了句“Best regards”。 当被中国同事笑着称为“同胞”时,他会轻轻摇头:“我是新加坡人。” 这个华人占比74%的国家,国徽上没有龙也没有凤,只有稻穗和狮子——前者象征多元种族的生计,后者代表城市的古称“狮城”。 为什么同样流着华人血脉,选择却如此不同? 马来西亚的橡胶园里,殖民时期的英国管理者曾禁止华人聚集,是私塾先生在椰树下偷偷教孩子写“人之初”;而新加坡独立之初,马来族、印度族与华族的人口比例接近,李光耀在国会强调“新加坡人优先”时,办公桌上摆着的是孙子用中文写的贺卡。 有人说新加坡华人“忘了本”,可春节时牛车水的红灯笼照样挂满整条街;也有人说马来西亚华人“太执着”,可他们的孩子同样唱着马来西亚国歌长大。 或许,没有绝对的“亲”与“疏”,只有在不同土地上长出的根——有的扎进了文化的泥土,有的缠紧了国家的岩石。 如今,陈阿水的孙子在吉隆坡开了家中医馆,墙上挂着“悬壶济世”的匾额,抽屉里却放着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执业执照;林明轩的女儿在新加坡华乐团拉大提琴,演奏《黄河协奏曲》时,琴弦震颤的频率里,藏着她在剑桥留学时被问“你从哪里来”的沉默。 那道关于“中华情感”的题,或许本就没有标准答案。 就像两棵从同一棵古树上分栽的苗,一棵在多雨的南方拼命往地下扎根,一棵在多风的海边努力向天空生长,根须与枝叶的方向不同,却都在自己的土壤里,活出了华人的模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