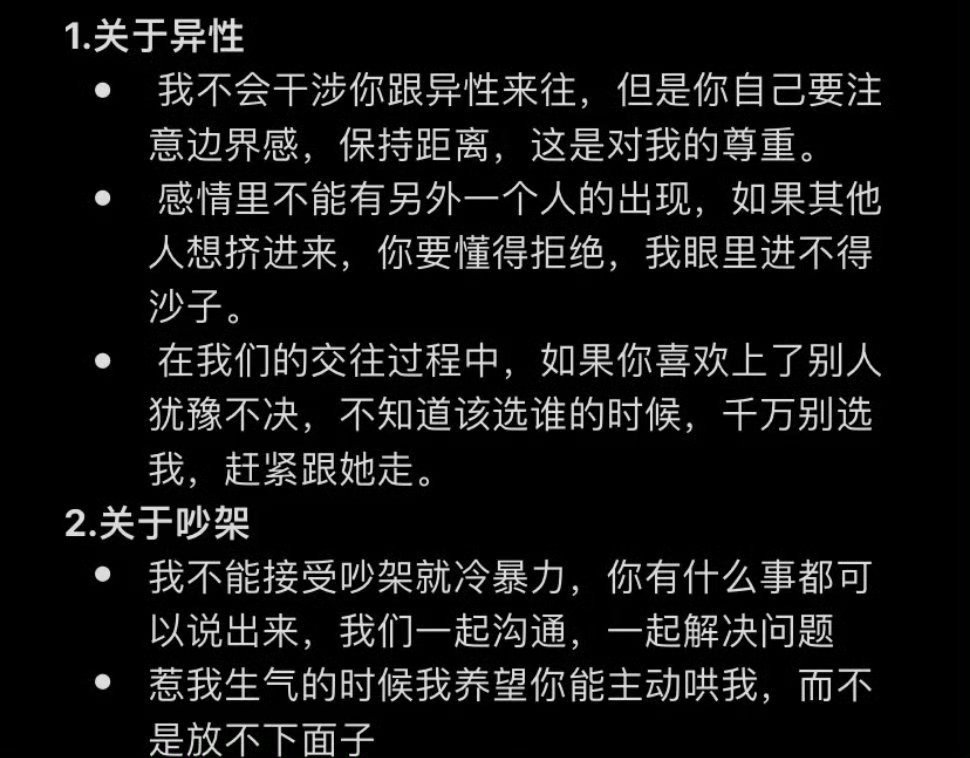1984年,丈夫刚在前线牺牲,她竟然就转身嫁给了丈夫的亲哥哥,而且让人不解的是,30年之后,她去祭拜前夫的时候,竟然抱着墓碑嚎啕大哭。 这种事放在哪个年代都足够让人议论半天,更何况是在那个对婚姻看得比啥都重的八十年代农村。 当时村里人的唾沫星子差点没把她家门槛淹了,有人说她嫌贫爱富,有人说她忘恩负义,可谢玉花就像没听见一样,每天照样扛着锄头下地,推着大伯哥的轮椅去村口晒太阳。 婚礼那天的红布还没来得及拆下,王长献的军装就已经被紧急集合令催得发烫。 谢玉花把刚煮好的鸡蛋一个个塞进丈夫背包,手指被烫得通红也没吭声。 本来想让他吃口热乎饭再走,可部队的马蹄声已经到了村口,两人就站在老槐树下抱着,谁都没说话。 后来听村里老人说,那天王长献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,军装后领都被扯得变了形。 不到半个月,骑着大马的通讯员就闯进了村子,绿色信封上的"烈士"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,把谢玉花的眼睛烫得生疼。 她疯了似的跑到供销社后面那条河沟,那是两人第一次说话的地方。 当时王长献帮她捞掉进水里的竹篮,裤脚湿了半截还嘿嘿笑,说解放军就该为人民服务。 本来想跟着丈夫一起走,可看着远处大哥王长明推着轮椅跌跌撞撞过来的样子,脚像灌了铅似的挪不动。 村里人都说谢玉花脑子坏了,放着好好的姑娘不当,偏要守着烈士的牌位和残疾的大伯哥过一辈子。 当时连她自己都觉得这日子没啥盼头。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,先给公婆烧好早饭,再推着大哥去村卫生室换药,回来还要侍弄那几亩薄田。 有次收玉米时下大雨,她一个人在地里抢收,滑倒在泥水里的时候,突然想起王长献说过退伍了要给她盖砖瓦房,屋檐下还要挂个红灯笼。 王长明其实一开始是拒绝的,他说自己这条腿残了,给不了她啥好日子。 可谢玉花铁了心,说这不是啥恩情,就是觉得这个家不能散。 婚后头几年最难熬,公婆身体不好常年吃药,小叔子小姑子还在上学。 她白天种地晚上编竹篮,手指磨出的茧子比男人的还厚。 有回供销社老板看她可怜,想多给点钱收她的篮子,她硬是按原价算,说长献在部队教的,做人得本分。 去年清明跟着志愿者去麻栗坡烈士陵园,谢玉花特意带了袋芝麻饼。 那是王长献最爱吃的,当年他总说等打完仗回来,要天天吃她烙的饼。 站在墓碑前,看着照片上年轻的笑脸,她突然想起婚礼那天他偷偷塞给她的红手帕,上面绣着歪歪扭扭的"平安"两个字。 三十年了,她把公婆养老送终,把小叔子小姑子都供成了大学生,连王长明的腿也在这些年慢慢能拄着拐杖走几步了。 现在村里没人再说闲话了,谁家有红白喜事都愿意找谢玉花帮忙,说她身上有股让人踏实的劲儿。 前阵子县民政局来人想给她办低保,她摆摆手说不用,现在政策好了,自己种的地够吃,编竹篮还能赚点零花。 她这辈子没做过啥大事,就是守着一个家,守着一句承诺。 那天从陵园回来,她在村口老槐树下坐了很久,风一吹,好像又听见当年长献说的那句"照顾好爹娘"。 如此看来,有些选择从来不是一时冲动,就像老辈人说的,日子是过出来的,不是说出来的。 谢玉花这辈子没穿过几件新衣服,没去过啥大地方,可她把一个破碎的家重新粘起来,让每个成员都活得有模有样。 现在她偶尔还会推着王长明去赶集,两人慢慢走在乡间小路上,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,就像当年她送长献参军时那样,只是这次,身边有了可以相互依靠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