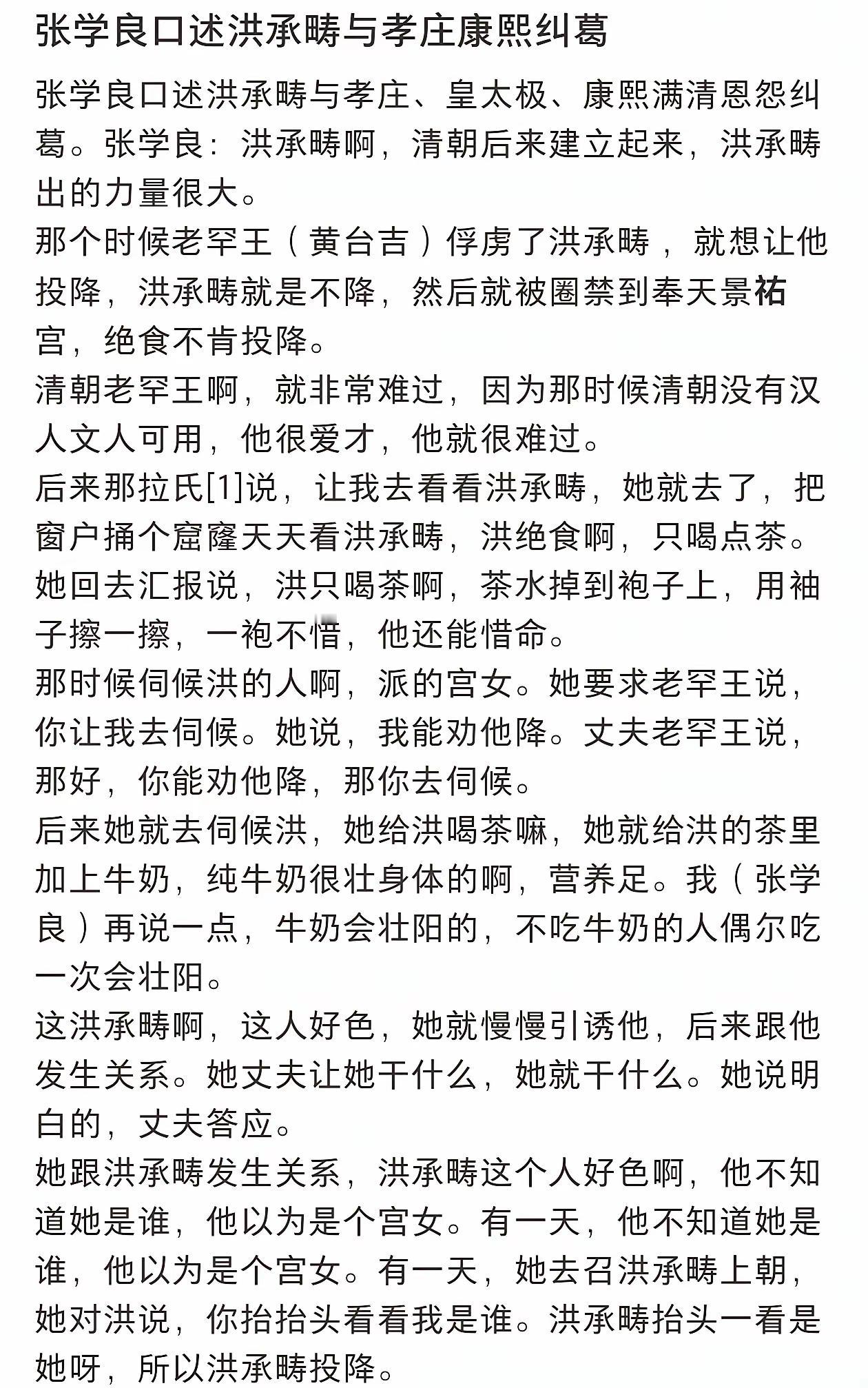溥仪三岁被抱进紫禁城的时候,怀里还攥着娘塞的虎头鞋。 他后来总说,那座金銮殿看着亮堂,金砖地却冰得像块铁——连阳光都照不透檐角的阴影。 十二岁那年的晚上,他刚把《论语》摊在紫檀木桌上,殿门就“吱呀”开了。 十几个宫女端着托盘进来,银碗里的参汤冒着白汽,蜜饯堆得像小山。 “万岁爷,奴婢们陪您玩‘猜花名’好不好?”领头的宫女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 他起先挺高兴,毕竟太监们总板着脸,宫女们的笑声像廊下的铜铃,脆生生的。 可玩到三更天,烛火都跳了,他揉着眼睛说“困了”,那只按在他肩上的手却没松。 “再陪我们会儿嘛,”另一个宫女往他嘴里塞了颗蜜饯,“天亮了让小禄子给您偷糖吃。” 外间的太监们在说闲话,铜火盆里的炭块“噼啪”炸出火星,他想喊人,喉咙却像被蜜饯糊住了。 后来他只记得那些晃动的人影,还有参汤灌进喉咙时的苦味——再醒来,日头已经斜斜切过窗棂,浑身软得像团棉花。 太医院的老御医搭脉时手抖了抖,开的方子只写着“静养”,临走前看他的眼神,像看件碰不得的瓷器。 可往后这样的“玩闹”没断过,有时太监也会进来,拿着“安神”的药丸说“皇上龙体要紧”,他把脸埋进枕头里,闻着那股陈檀香,忽然觉得这龙袍还不如街边乞丐的破棉袄自在。 老太监孙耀庭晚年说“宫女们把皇上当玩意儿摆弄”,可也有人说那时宫里早乱了套——隆裕太后没了,摄政王不管事,下人们照着老黄历上的“伺候规矩”行事,只是忘了规矩里该有的敬畏,只剩下些走了样的殷勤。 那些被硬灌下去的参汤和药丸,太医院不敢写“虎狼药”,只说是“温补”,可少年人的身子哪禁得住这样的“补”?就像把嫩苗往烈日底下晒,看着精神,根早就枯了。 后来他娶了婉容,夜里总梦见一群穿宫装的人影追着他跑,婉容披衣坐起来,问他怎么了,他只翻过身说“没事”——有些疼是说不出口的,一说,那点可怜的自尊就碎成渣了。 日本人弄他去长春当伪满皇帝时,医生说他“龙体欠安,恐难有子嗣”,他捏着那份诊断书,指节泛白,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的夜晚,要是当时能哭出来就好了,可那时候连哭的力气都没了。 战犯管理所的夜里,他常梦见紫禁城的雪,雪片子落在琉璃瓦上,悄无声息,就像那些夜里他不敢哭出的声音。 晚年和李淑贤逛公园,秋阳把草坪晒得暖烘烘的,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追着蝴蝶跑,笑声像撒了把碎银。他站在那儿看了好久,直到李淑贤碰了碰他的胳膊,才叹口气说:“要是那年冬天,我也能在雪地里追着风筝跑就好了。” 李淑贤没说话,只是把他的手往自己棉袄口袋里揣了揣。他的手很凉,像揣着块从紫禁城带出来的冰,这么多年,总也捂不热。 1967年他走的时候,窗外的玉兰花刚打骨朵,李淑贤说他最后嘟囔了句“想喝碗热粥”——就像十二岁那个早上,他醒来时最想喝的,也是碗加了姜丝的热粥,可宫里的粥永远是甜的,甜得发腻。 他的骨灰葬在华龙皇家陵园,离紫禁城很远,远得能听见风吹过麦田的声音。 有人说他这辈子值了,当过皇帝坐过牢,最后成了普通人,可只有李淑贤知道,每个清明她去看他,墓碑上的照片里,他眼角那点化不开的郁色,和十二岁那年从噩梦里醒来时,一模一样。 那些藏在金碧辉煌背后的疼,像紫禁城地砖缝里的草,不见天日,却在他心里长了一辈子——谁又能说,权力和牢笼,不是一回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