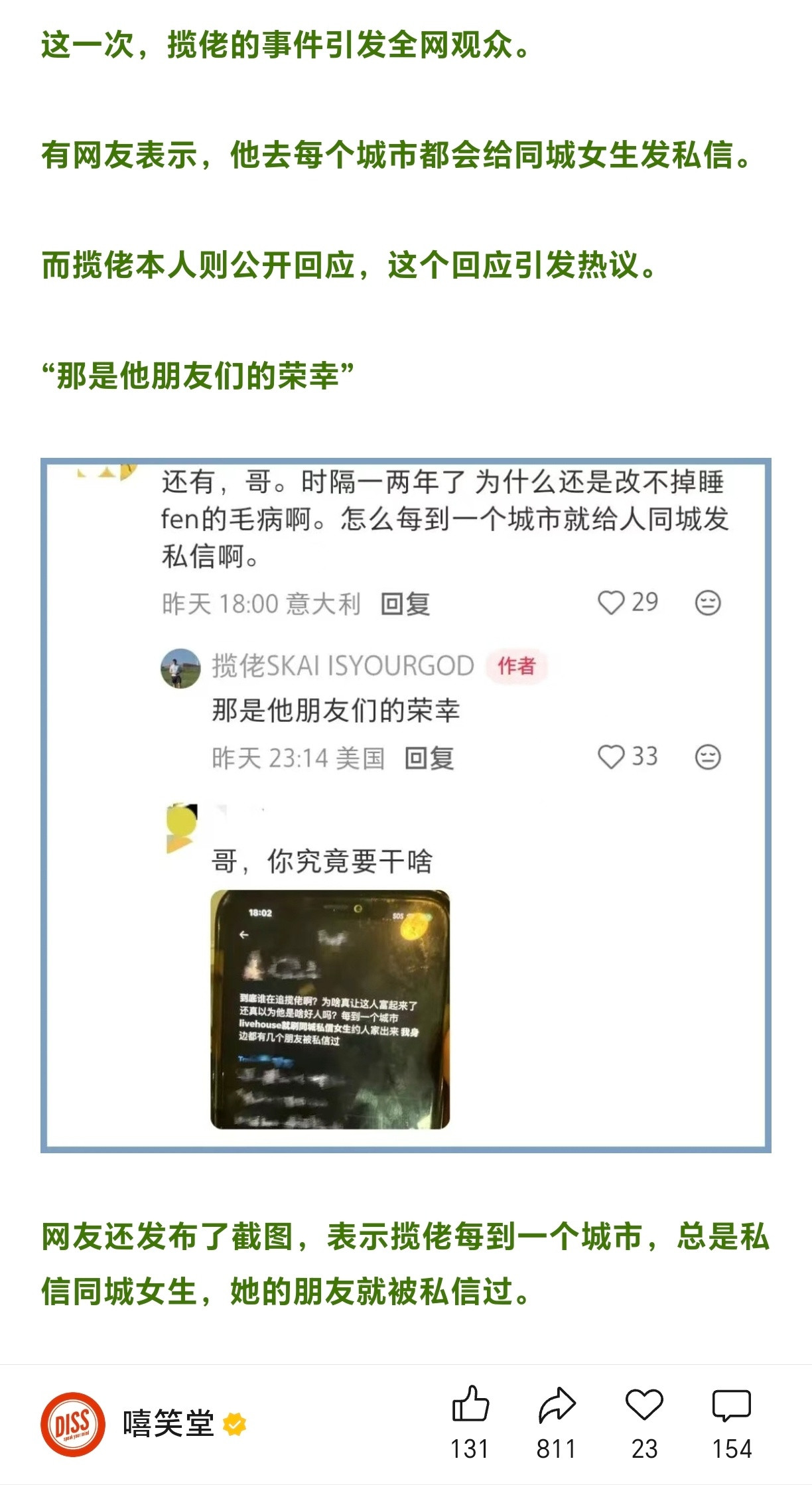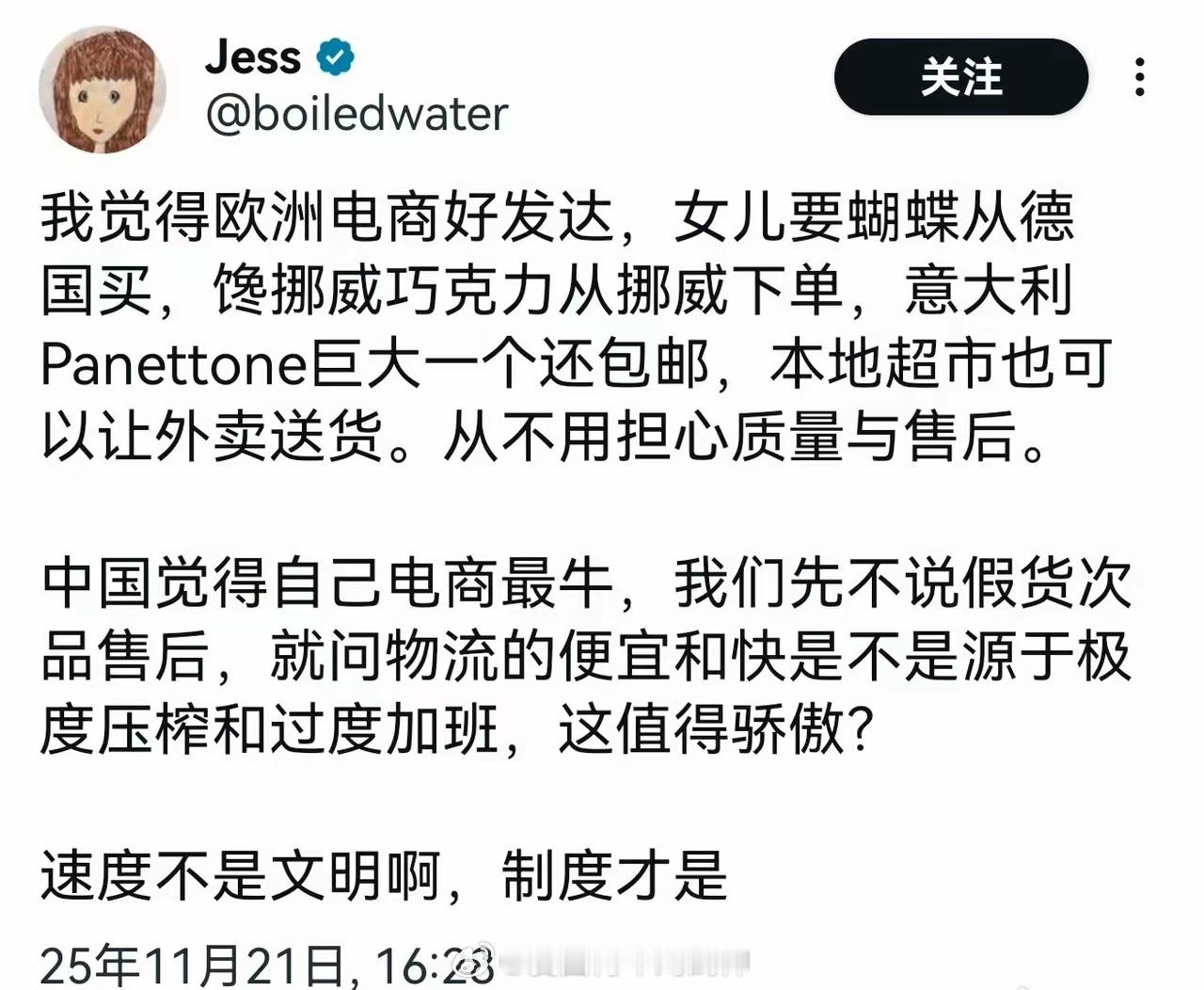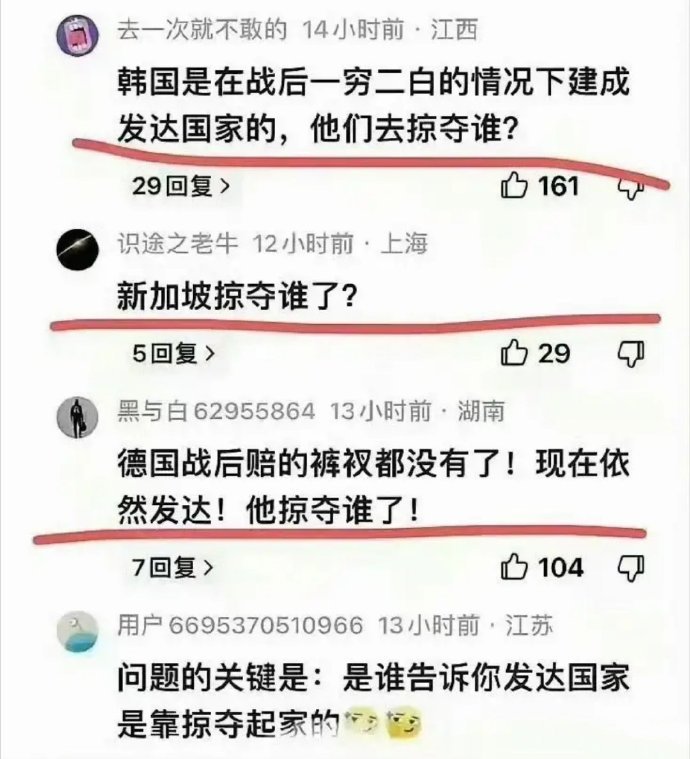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?不夸张地说,安乐死一旦被放开,那就是穷人的噩梦…… 在荷兰,一位老年工人因无力支付癌症治疗费用,最终选择通过安乐死“体面”离世,但他最后一句话却令人心头一紧:“我不是想死,是活不起了。” 如果说安乐死是“选择的自由”,那问题来了:谁真的有资格“自由地”选择死亡? 安乐死听起来是个美化过的词,“有尊严地离开”,但在现实中,它往往不是“选择”,而是“无路可选”。 尤其是在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均衡的国家,安乐死一旦合法,对穷人来说很可能从“权利”变成“义务”。 医生本该救人,而不是决定谁该活、谁该死,这不是一句口号,而是医学伦理的底线,可一旦安乐死成为合法选项,那些无法负担昂贵治疗的病人,真的还能等到奇迹吗? 还是说他们会被“劝退”去追求一种“看起来体面”的死亡? 在荷兰,2024年公开的六起非法安乐死案件中,有患者根本没有被充分评估心理状态就被“执行”了。 这说明什么?说明制度再完善,也有缝隙,而一旦生死被程序化处理,穷人就可能沦为这套系统里最容易“走流程”的那批人。 安乐死不是一个按钮,按下就完事,它背后需要强大的制度支撑、法律监管和职业伦理,然而现实是,就连制度最完备的荷兰和比利时,也时不时爆出安乐死被滥用的案例。 更别说那些医疗体系本就脆弱、法律监管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了。 比如南非,2019年曾就安乐死展开讨论,但最终搁置,理由很现实:目前连基本医疗都难以普及,又如何保障安乐死的“合规”? 一旦制度跟不上,安乐死就可能变成“便宜了事”的手段,不是为人性负责,而是为预算减负。 而且,谁来决定你“够不够痛”或者“够不够绝望”?是医生?家属?还是保险公司?只要这个判断标准存在模糊地带,就意味着可能被操作、被误解、甚至被利用。 在比利时和加拿大,已经有研究发现:安乐死申请者中,低收入人群、孤寡老人、残障人士占比远高于中高收入人群。 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在“选择死亡”的背后,常常不是因为身体痛苦到不可忍受,而是因为生活陷入了无解的困境。 当活着的成本高到压垮你,而死亡却变成“最便宜的解脱方式”,这还叫“自由选择”吗? 安乐死在富人眼里也许是“体面离场”的权利,但在穷人眼里,它可能只是“穷到连活着都负担不起”的无奈。 去问问那些年迈独居、无医保、无亲属照顾的人,他们想不想活下去?大多数人都想,但他们没有资源撑到生命自然结束。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,包括德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意大利,始终对安乐死保持高度保守的态度。 因为他们知道,一旦这个口子开了,最先涌进去的,不是那些真正无法忍受病痛的少数人,而是被社会遗忘的多数弱者。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表示,临终关怀应当成为各国医疗系统的重要部分,而不是让那些没有医疗、没有陪伴、没有希望的群体“自己找个出口”。 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安宁疗护体系的建设,就是希望让每一个人直到最后一刻都能被善待,而不是被“处理”,真正的文明社会,是让人有尊严地活到最后,而不是丢给一个“安乐死协议”就了事。 这也是为什么,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:生命至上,慎之又慎,不是不尊重个人选择,而是要先确保这不是“被迫的选择”。 如果连基本医疗、心理支持、长期照护都无法保障,那谈什么“自愿死亡”?有多少“自愿”,其实是“活不下去”的变形表达? 一项法律的出台,不只是技术问题,更是价值排序的体现,安乐死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开与关”的问题,而是对社会底层安全网的终极考验。 如果社会不能给人一个好好活着的理由,那就别轻易给人一个“体面死去”的选项。 别让“安乐死”变成替代医疗、公平、照护的快捷方式。那不是人道,而是冷漠。 真正的进步,不是让死亡变得更方便,而是让活着变得更有尊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