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敢信?北宋嘉祐二年的科举考场,藏着史上最牛“神仙天团”——主考官是大文豪欧阳修,考生里有后来“一门三学士”的苏洵之子苏轼、苏辙,还有“唐宋八大家”里的曾巩;更离谱的是,理学泰斗程颢、程颐兄弟,以及说出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”的张载,全在同一考场拼杀。 可谁能想到,这届被后世称为“千年龙虎榜”的科举,殿试放榜那天,状元竟是个当时没啥名气的“小透明”章衡,连苏轼都服气感叹:“子平之才,百年无人望其项背。” 现在网上总有人替苏轼鸣不平,觉得这状元肯定是走了狗屎运。但你要是翻翻当时的科举流程,再扒拉扒拉章衡的底细,就知道这“冷门”俩字儿有多站不住脚。 北宋科举分三级:先解试考资格,再会试筛人才,最后殿试定名次。欧阳修当的是会试主考官,负责从全国考生里挑出顶尖苗子送进殿试。 这回他改革文风憋足了劲——之前流行的“太学体”文章,辞藻堆得比房梁还高,内容却空得像漏风的破碗,跟现在某些“学术黑话”一个德行。所以他在会试阅卷时专挑“干货多、能落地”的文章,那些花架子分分钟被打回原形。 章衡是福建人,放现在绝对算“高考大省”出来的狠角色。他的会试策论写的是啥?史书记载“论时务,指陈切直”,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直戳北宋三大痛点:官员多到冗余、边防漏洞百出、老百姓日子过得苦哈哈。 每条问题都像刀刻似的扎心,更绝的是他还给出了具体解决办法——怎么精简机构、怎么加固边防、怎么轻徭薄赋,条理清晰得跟现在的可行性报告似的。欧阳修天天看“之乎者也”没营养的文章,突然来这么一篇“带着泥土味儿”的实诚文章,能不眼前一亮吗? 再看苏轼,他的会试文章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确实牛,情理交融得能把阅卷老师的泪腺戳漏。梅尧臣看完直接拍大腿,拿红笔圈了又圈,连夜推荐给欧阳修。 可欧阳修一看,以为是自己学生曾巩写的——毕竟曾巩的文章也以沉稳著称——怕落人口实,愣是把这篇本该会试第一的文章压成了第二。 后来知道是苏轼,欧阳修不仅没红眼,还逢人就说“老夫当避此人,出人头地矣”。但会试只是“入围赛”,真正的“终极排名”在一个月后的殿试。殿试由宋仁宗亲自主持,苏轼到底拿了第几名? 史书记载他殿试考了乙科,具体名次没明确说“第二”,但肯定进了一甲——毕竟后来他成了“唐宋八大家”,官也做到宰相级。不过这届殿试的头名,确实是章衡。 再说章衡后来的日子。这哥们儿可不是“一考定终身”的幸运儿,当官后干了不少硬核实事:出使辽国时,辽人想用高规格礼仪压宋朝,章衡当场怼回去:“南北虽异,礼仪岂有尊卑?”硬是给大宋争回了面子;在地方上当市长,修水利、减赋税,老百姓至今还在当地县志里记着他的好。 后来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,专门提过他的政绩——“衡所至,人皆思之”。你看,这哪是“冷门状元”?分明是实力派的低调发言。 现在总有人爱喊“怀才不遇”,可你仔细想想,真正有本事的人,什么时候需要靠“抱怨”刷存在感? 苏轼被贬黄州,没抱怨,写出了《赤壁赋》;王安石变法受挫,没抱怨,继续研究经学;章衡没当殿试状元(会试第二),没抱怨,在各个岗位上把本事使到了极致。 所谓“怀才不遇”,大多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感慨——要么是自己没抓住机会,要么是没本事让别人看见,偏要找个“运气不好”的借口。 那天翻《宋史》,看到章衡晚年退休,回到福建老家,子孙绕膝,当地百姓自发来拜见。他摸着胡子笑:“我这一辈子,没白活。” 突然就懂了:真正的“遇”,从来不是某个位置、某个头衔,而是你的本事能被时代需要,你的价值能让众人看见。如果整天喊“怀才不遇”的人,不妨问问自己:我要是章衡,能在策论里写出解决问题的实招吗?要是苏轼,能在被压名次后还能写出传世文章吗?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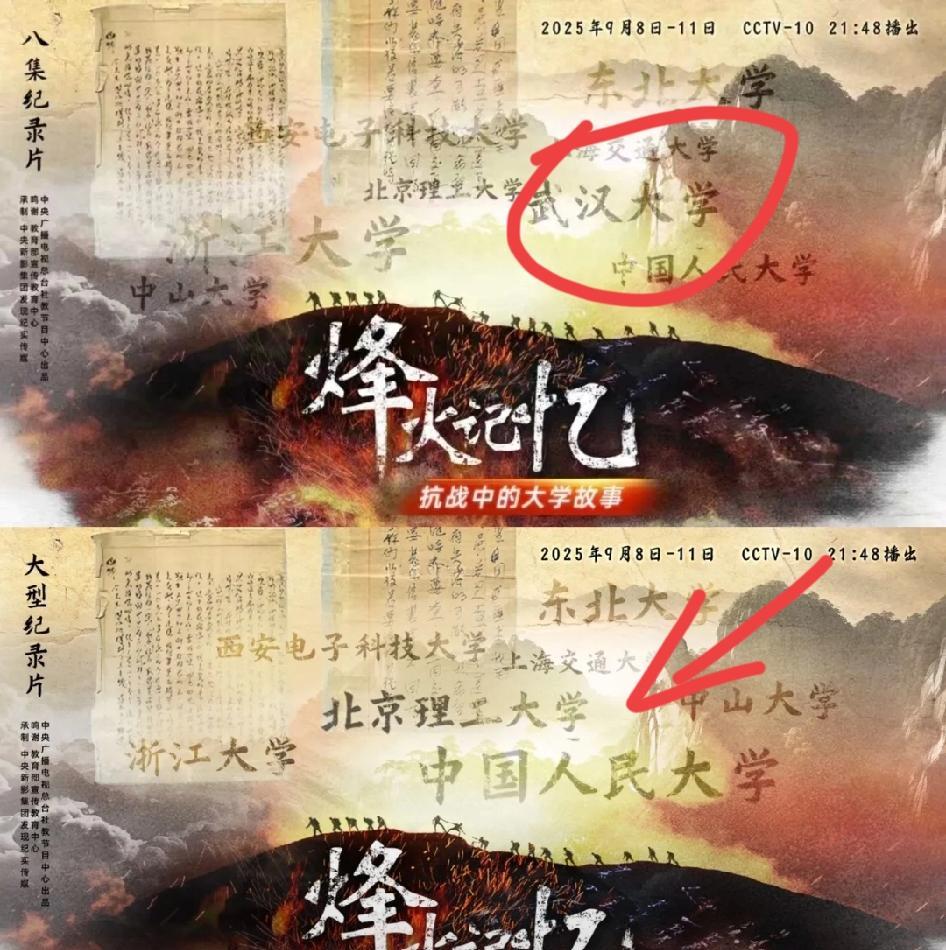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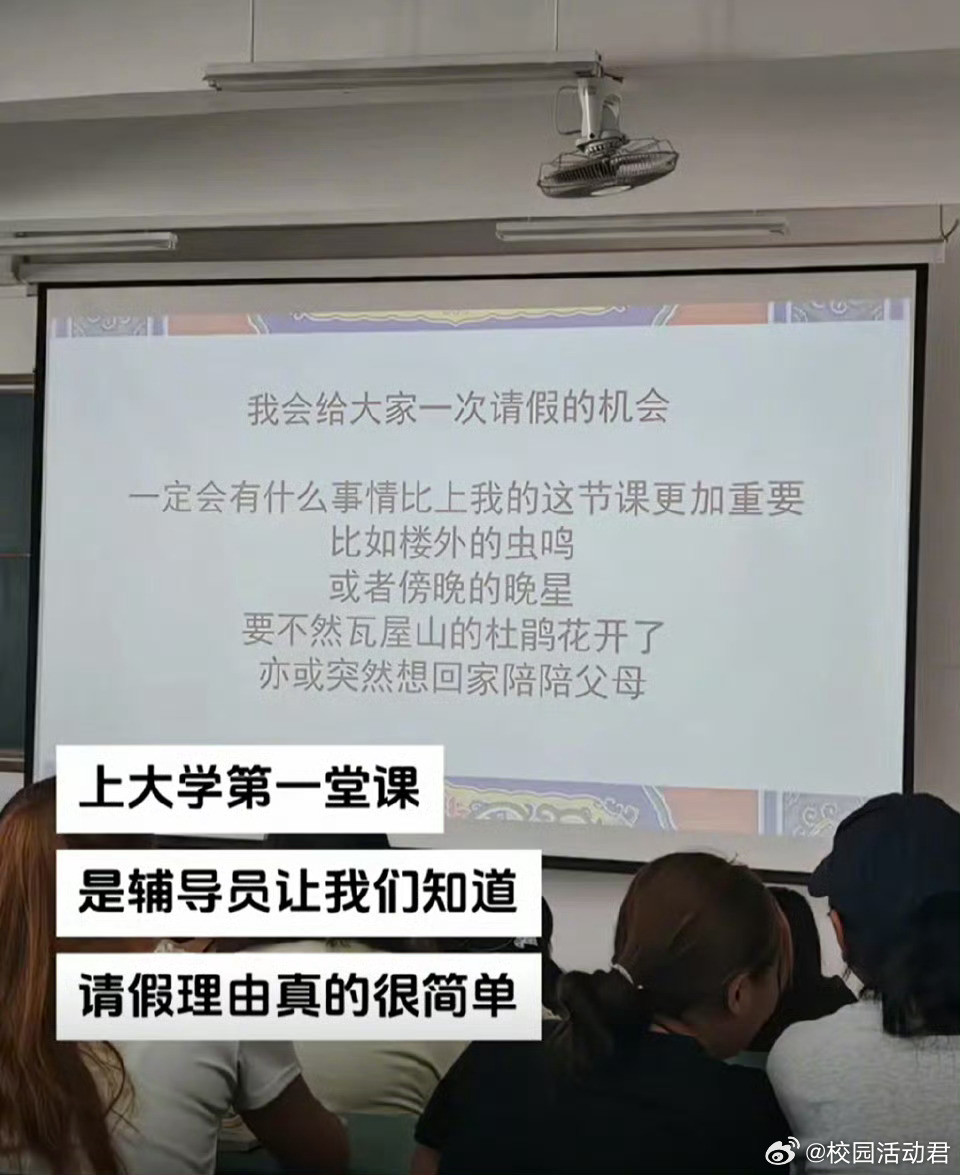
![遇到30多岁的保守女生,怎么办?[思考][思考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3126929810398686203.jpg?id=0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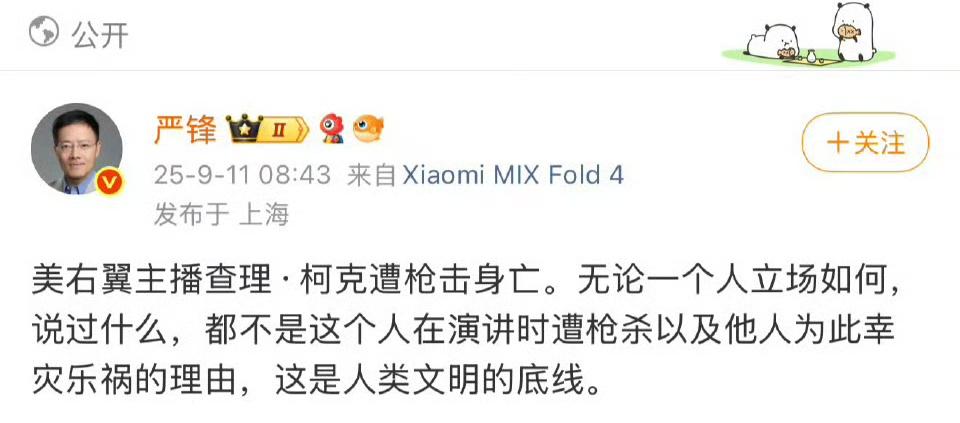
![明朝的刘瑾能坚持那么久也是个狠人[吃瓜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9087977612433242875.jpg?id=0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