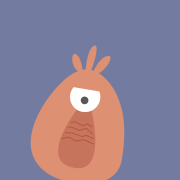观众席最后一排,灯暗处。 巍子坐着,像块沉默的礁石。 台上毕业大戏正酣,他儿子在光里。 没人知道他是谁的父亲。 三年前,可不是这样。 美国。 豪宅。 账单雪片般飞来。 儿子电话里还是那套:“爸,打点钱。 ” 巍子买了张单程票。 面对面,儿子叼着雪茄。 他掏出的不是支票,是一张撕成两半的副卡。 “你的游戏,结束了。 ” 机票甩过去,“跟我走,或者留下,自己选。 ” 儿子选了留下,以为老头心软不过三天。 苦头来了。 信用卡全停。 从大house滚去地下室合租。 端盘子,手被洗碗水泡得发白。 送外卖,在暴风雪里摔得鼻青脸肿。 最饿的时候,和流浪汉分一个冷罐头。 他第一次懂了,钱不是数字,是汗,是疼,是尊严的标价。 他拨通那个没删的号码。 “爸,我回去考中戏。 考不上,我认。 ” 不是求救,是通知。 巍子挂了电话,对着窗外,站了一夜。 中戏考场,他报名用的本名,王紫逸。 考官眼皮都没多抬一下。 他靠一段送外卖被骂的独白,拿了那一届的表演专业最高分。 校内话剧奖,他捧回奖杯,室友才知道他是巍子的儿子。 有剧组直接递来男二合同,他推了。 “从场记,从有一句台词的角色开始,行吗? ” 副导演像看怪物。 如今,教育专家在电视上侃侃而谈,说这是“挫折教育”的范本。 巍子从不看这些节目。 他只看戏。 戏散了,他压低压低帽檐,从侧门悄悄离开。 台上,他儿子正和同学拥抱,灯光照亮他汗湿的额头,那光亮,是他自己挣来的。 最好的父爱,有时不是托举,而是毅然抽走那块虚假的地板。 让他坠落,让他触底,然后,看他自己从尘土里,长出一根坚硬的脊梁。 这道理,不是教出来的,是活出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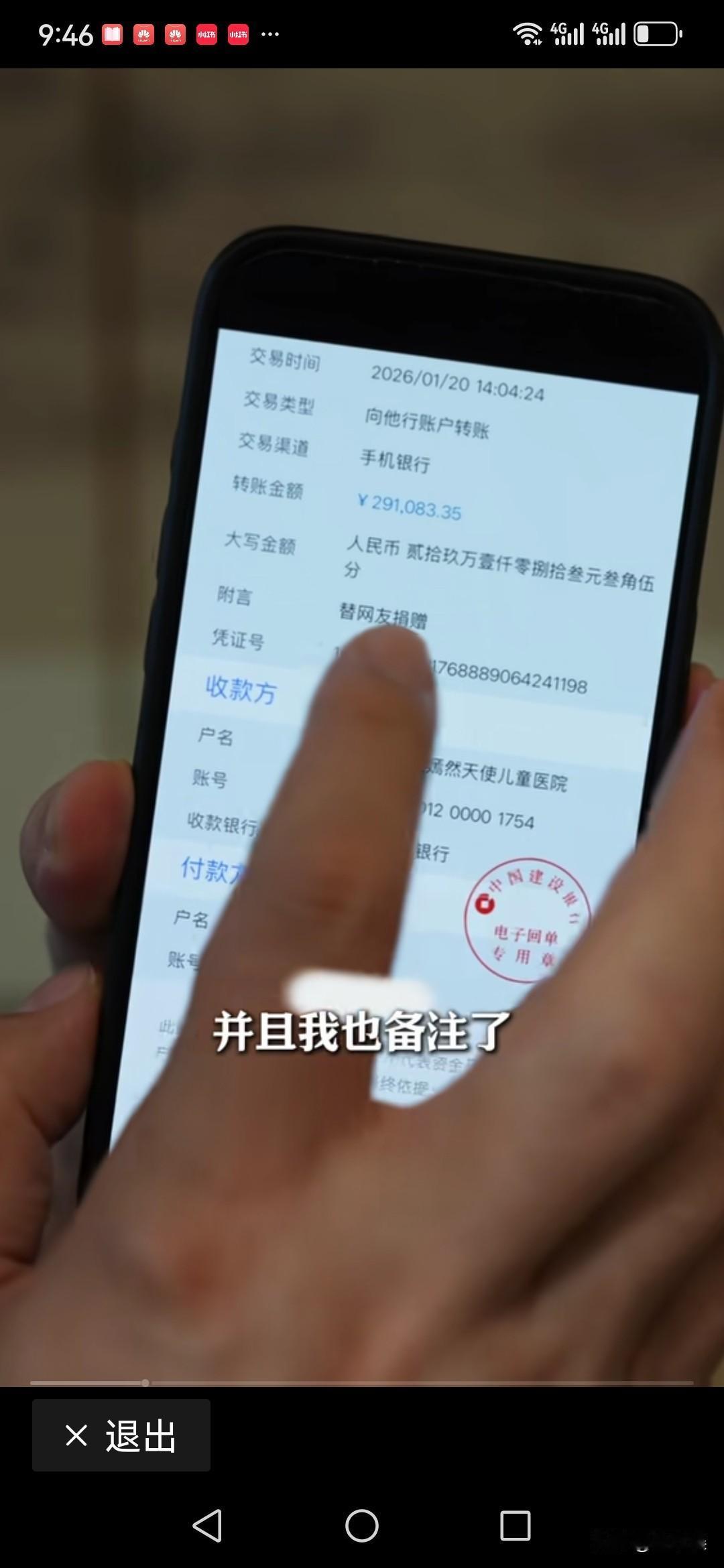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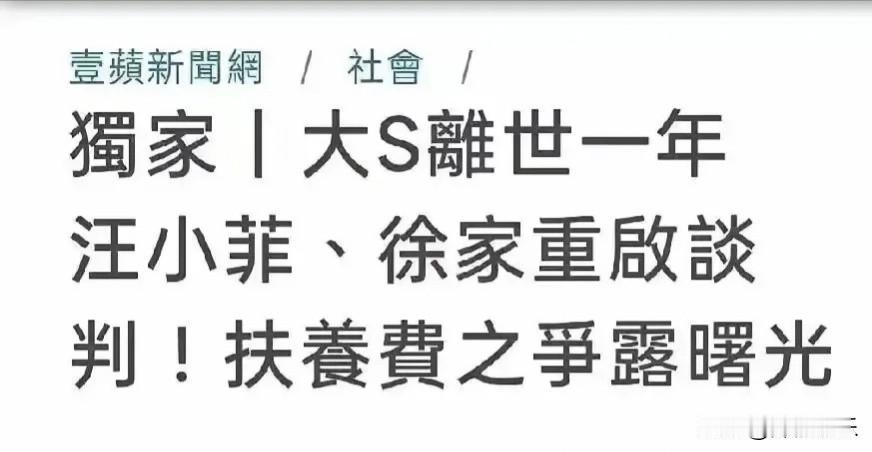
![是谁这么有才,把原图(p1)给整成了p2……[笑着哭]来来来,你站出来,王一博保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6536009819446252961.jpg?id=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