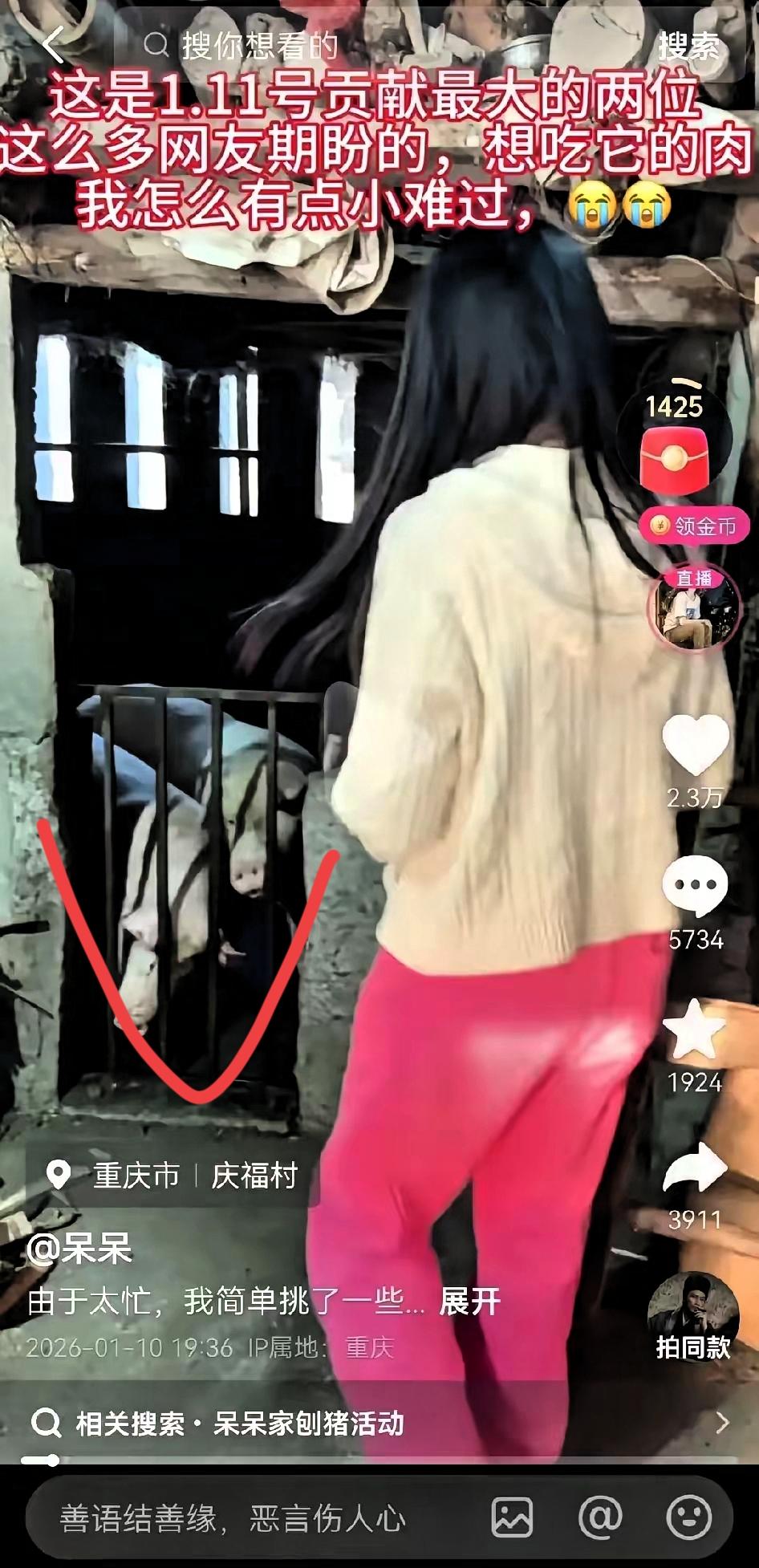1998 年,一古稀老头和寡妇正在床上翻云覆雨,正当俩人难舍难分的时候,却被人一脚踹开了房门,没想到老头一点也不慌张,不紧不慢的穿上裤子之后,便乖乖跟着警察走了。 我跟你说,这事儿是翠娥婶子去年蹲墙根跟我唠的,那细节说得,连警察靴筒上沾的泥点子个数都能数出来。当时她吓得连气都不敢喘,抓着被子往脖子底下缩,煤油灯被踹门的风刮得直晃,灯芯“滋啦”一声冒了个火星,把房梁上挂的干豆角烧了个小口子。警察的黑胶鞋踩在泥地上,带进来的雨点子溅到她脚背上,凉得她一激灵。 那老头是前年来的,一开始在村西头破庙住,后来帮翠娥婶子修漏雨的鸡棚,修着修着就修到她炕头去了。没人知道他大名叫啥,大伙都喊他老陈,他也应得爽快。 老陈系腰带的动作慢得要命,铜扣“咔嗒”一声扣上,还顺手把翠娥婶子滑到胳膊肘的被子往上拉了拉,才转身。走到门口时,领头的警察已经不耐烦地敲门框了,他却突然回头,从怀里摸出个磨起毛的蓝布小包,塞到她手里,指节上的老茧蹭得她手心发痒。“等我走了再看。”他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,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跟着警察走了,连伞都没拿。 门“砰”地关上,外面的雨声裹着摩托车的突突声,越走越远。翠娥婶子攥着布包,指节都捏白了,过了半天才敢打开。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毛票,用麻绳捆得紧紧的,还有个油纸包,打开是半块粘了芝麻的桃酥——上周她赶集时给他买的,他说甜得牙疼,却还是揣兜里没舍得吃。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,上面是个穿粗布褂子的年轻姑娘,扎着俩麻花辫,站在老槐树下笑,背后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:“秀莲,1962年冬”。 后来派出所来人才说,老陈当年是个木匠,给邻村盖房时,房梁塌了砸死了人,他怕赔不起,就揣了半个窝头跑了,这一跑就是三十多年。秀莲是他媳妇,当年怀着娃等他,娃没保住,她也熬坏了身子,没两年就走了。他这些年在外面打零工攒的钱,本来是想攒够了去秀莲坟前赔罪的,结果碰到翠娥婶子,觉得最后这两年有人给暖被窝,也值了。 你说这人啊,这辈子谁没点躲不开的坎?可欠了的债,早晚都得还,躲了半辈子,最后不还是得站出来给人一个交代?
【琅河财经】一名曾经的警察自述:我讲个真实案件,介意的朋友不用看。大概是20年
【11评论】【16点赞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