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7年,43岁的军阀陈镇山娶了19岁的女学生柳月娥。洞房当晚,陈镇山把怀表往桌上一拍,对柳月娥说:“衣服不用脱了,你就在这屋睡。明早去给夫人磕头,以后家里事都听她的。”说完扣上军装扣子,转身就往原配赵玉蓉的院里走。 柳月娥僵在原地,桌上的洋油灯芯滋滋响,火苗晃得满墙影子都在动。她没脱嫁衣,就着床边坐了一夜。 第二天给夫人赵玉蓉磕过头,日子便定了型。她像件摆设,被安置在后院一个小房间里。陈镇山再没来过,赵玉蓉也淡淡的,只让她每日晨昏定省,其余时间不许乱走。她带来的几本旧书翻得起毛,窗外的树叶子绿了又黄。 转眼到了深秋。一天夜里,柳月娥被急促的拍门声惊醒。开门一看,是赵玉蓉身边的老妈子,脸色煞白:“夫人咳血了,老爷不在府里,请大夫的兵还没回来……” 柳月娥跟着跑到正房。赵玉蓉歪在榻上,手帕上一团暗红,人却还清醒。看见柳月娥,她喘着气说:“柜子最底下……有个铁盒子,拿来。” 柳月娥找出盒子。赵玉蓉哆嗦着打开,里面是一沓信,最底下压着张照片——两个穿学生装的姑娘,挽着手在湖边笑。年轻的那个,眉眼像极了柳月娥。 “这是我妹妹,”赵玉蓉摩挲着照片,“十年前病死了。你刚进门那天,我就瞧着你像她。”她抽出最上面一封信,递给柳月娥,“念。” 信是陈镇山从前线寄回的,字迹潦草,只说战事紧,让玉蓉保重身体,末尾添了句:“新来的那个小丫头,若闲着,可让她帮你读读报,写写回信。” 柳月娥念完,屋里静得很。赵玉蓉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天,忽然说:“他这人,心里装的事太多,话又懒得说全。”顿了顿,“明日开始,你上午来我这儿,帮我看信、写回帖吧。” 从那天起,柳月娥的生活有了变化。她每天上午去正房,赵玉蓉教她理账、看人情往来的帖子。两人话不多,常是一个靠榻养神,一个伏案写字,只有毛笔划过纸的沙沙声,和窗外偶尔掠过的鸟鸣。 腊月二十三,陈镇山突然回来了。风尘仆仆,军大衣上带着寒气。晚饭时,他瞥见柳月娥手边一本摊开的账册,字迹工整清晰。他没说话,只多看了一眼。 那晚,柳月娥照旧回自己小屋。睡前,她发现桌上多了块新手表,下面压着张字条,是赵玉蓉的笔迹:“过年了,添个新的。怀表老了,走得不准。” 她把旧怀表和新手表并排放着。夜深了,两只表的滴答声轻轻合在一起,像这个院子里终于找到节奏的心跳。
惨不忍睹,南京姑娘遭到日军一个小分队的轮奸。这不是虚构的惨剧,是1937年
【9评论】【44点赞】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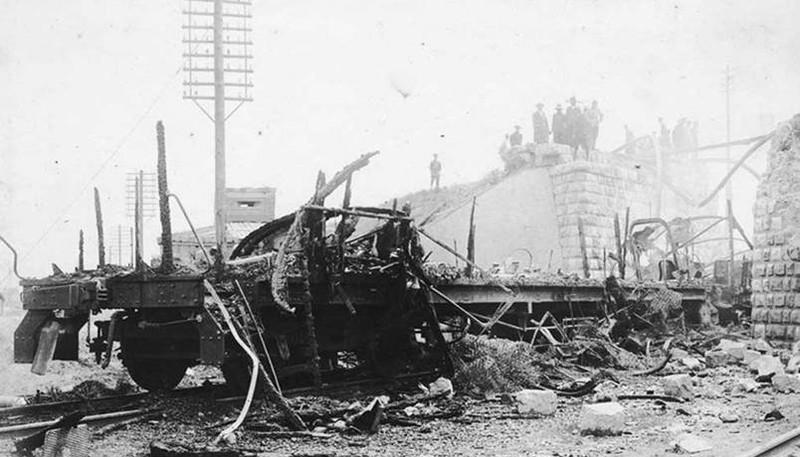

火山
莫名其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