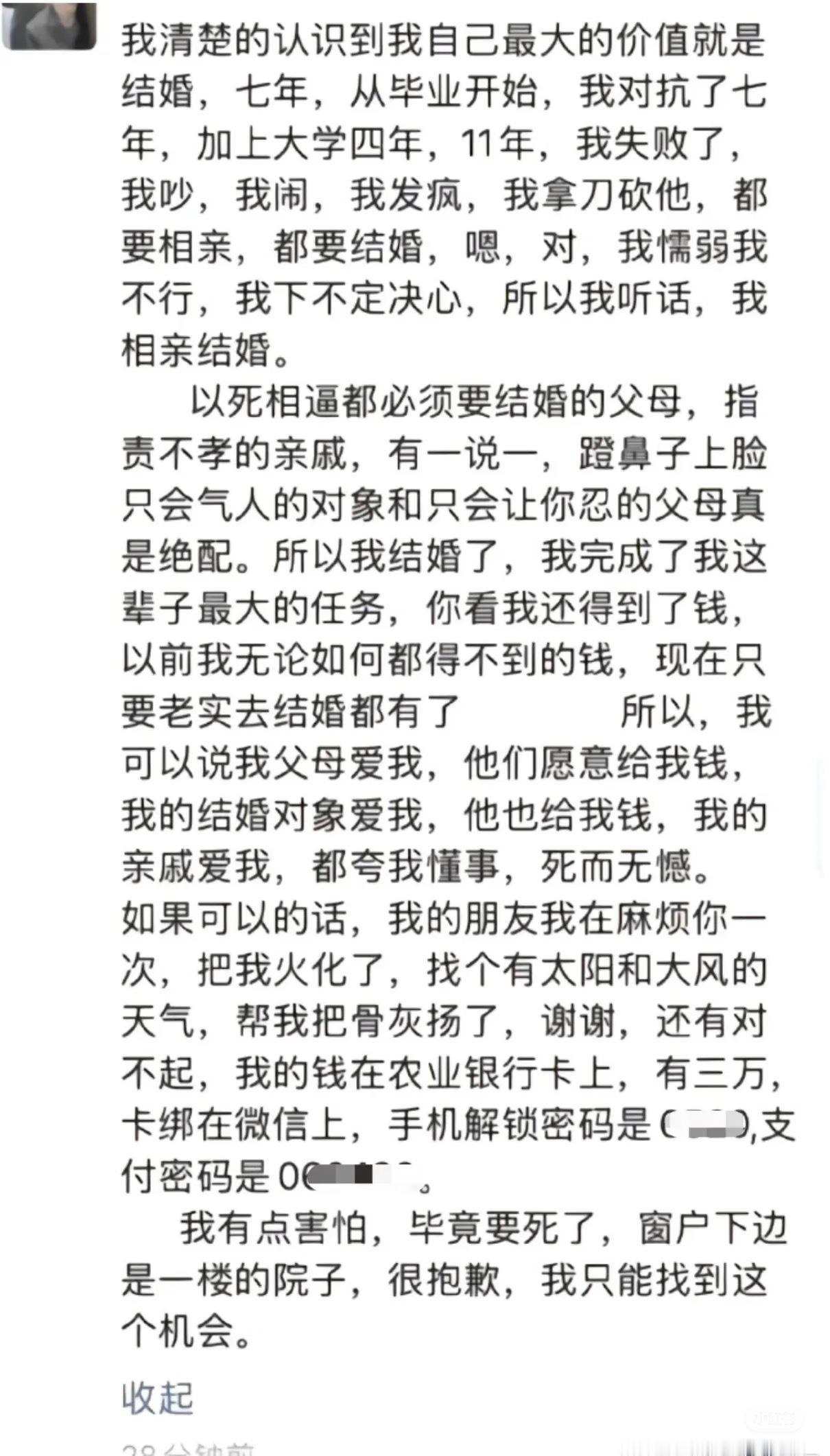高考结束后,男孩向女孩表白了,女孩拒绝了他,因为她考了700多分,去上了985名校,而男孩考的并不理想! 我蹲在工地的阴凉处啃馒头,汗水顺着安全帽的边缘滴下来,在砖地上洇出深色的圆斑。手机突然震动,班级群弹出条消息:校花在朋友圈晒了北大未名湖的照片,配文“新起点”。馒头卡在喉咙里,噎得人眼眶发酸。 后来我没复读,去汽修厂当了学徒。师傅话少,就让我整天拧螺丝,拧得虎口发麻。冬天冷,手裂了口子,沾到机油,疼得钻心。有回给一辆白色轿车做保养,车里飘出股栀子花味儿,和我高中时在她头发上闻到的一模一样。我手一抖,扳手差点砸在车漆上。车主是个中年女人,瞥我一眼,没说话。车开走的时候,我盯着尾气发了半天呆,心里空落落的。 再听说她的消息,是两年后了。老家同学说,她北大没读完,休学了。具体为啥,谁也说不清。有人说她跟不上,压力太大;也有人说家里出了事。我摸出手机,点开那个早就不用的QQ,她的头像灰着,签名还停在四年前:“奔赴山海”。 去年冬天特别冷,我那小修理铺的暖气片咣当咣当响。门帘一掀,她走进来,裹着件旧羽绒服,脸冻得通红。我俩都愣那儿了,谁也没先开口。铺子里就剩下暖气片的杂音,还有窗外风吹过电线呜呜的响。最后她搓搓手,哈出口白气:“车胎扎了,能补吗?” 补胎的时候,我蹲着,她站着。影子在水泥地上叠在一块儿,又分开。她忽然说,北京冬天干,她老流鼻血;说未名湖的冰结得厚,但滑起来没老家河沟自在;说那些听不懂的课,像天书。她说这些的时候,语气平平的,像在讲别人的事。拧完最后一颗螺丝,我站起来,膝盖咔吧一声。她递过来一瓶水,塑料瓶,还是凉的。 后来她常来,有时是车真有问题,有时好像就是过来坐坐。我修车,她就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看书,看的是些我从没听过的书名。阳光从油腻的窗户照进来,光柱里灰尘打着旋儿。有次她看着看着睡着了,头一点一点的,书掉在地上。我捡起来,页角密密麻麻全是笔记,字迹工整,像她从前那样。 春天的时候,她说要回去了,手续办好了,接着把书读完。那天傍晚她来道别,夕阳把铺子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她递给我一个小盒子,里面是枚北大的旧校徽,边角有点磨亮了。“这个……没别的意思,”她抿抿嘴,“就是觉得,该物归原主。” 她走了以后,我把校徽钉在墙上,和那些扳手、钳子挂在一起。有时候抬头看见它,会想起高三那个闷热的晚自习,电风扇吱呀呀地转,她隔着过道扔过来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“明天加油。”字迹被手心的汗洇开了一点。 你看,路走着走着,好像又绕回了某个似曾相识的岔口。只是不知道这次,风吹往哪个方向。
高三妈妈的崩溃昨晚1点把娃房间的灯关了,自己坐在客厅偷偷掉眼泪,感觉当妈这么多
【17评论】【7点赞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