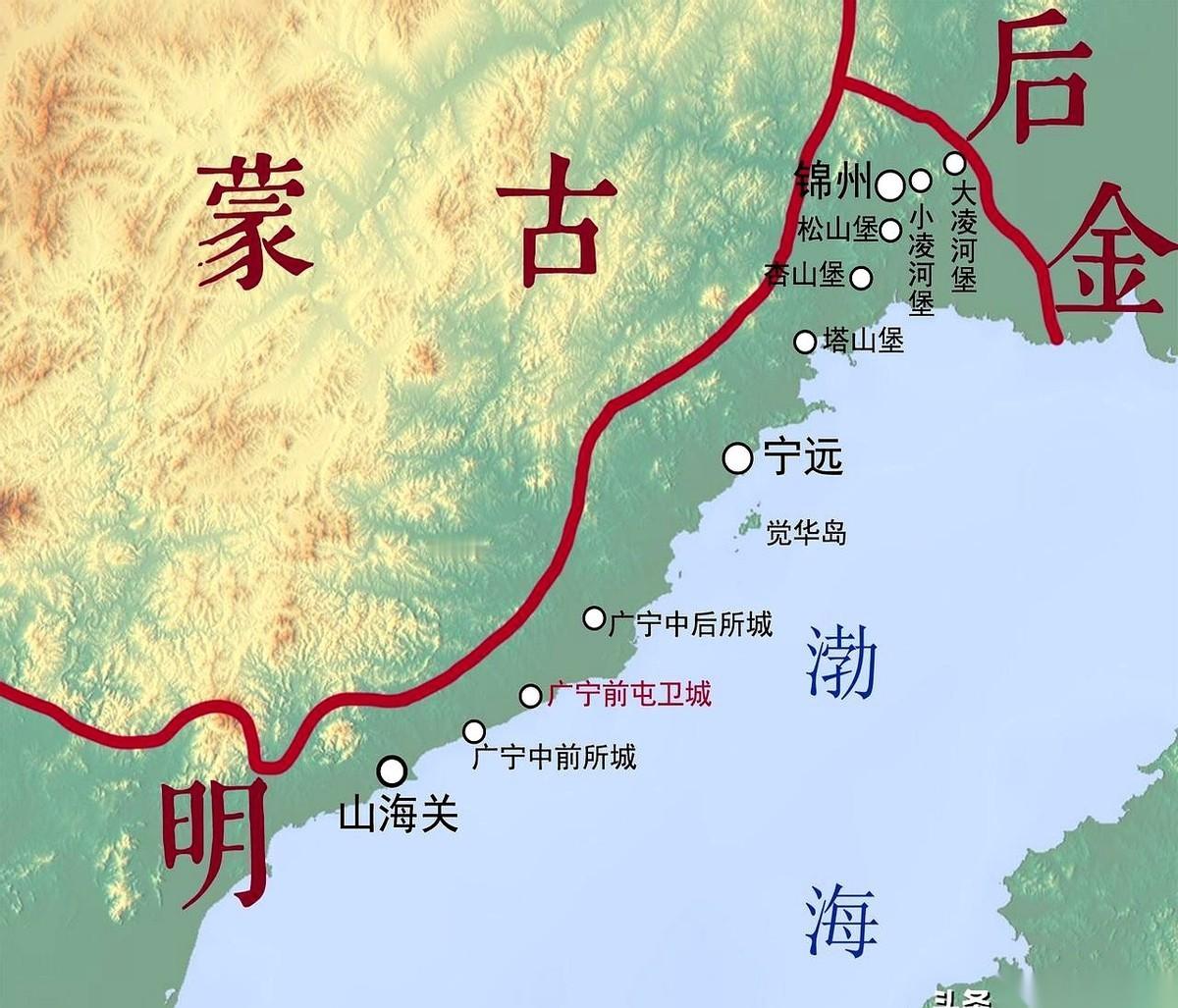公元9年,西汉太后王嬿正躺在自己的寝殿里闭目养神,忽听榻旁有男人的声音说:“微臣奉诏前来请脉。”王嬿将手伸出帘帐,不料却被男人一把握住,只听男人道:“太后年少寡居,难道不寂寞吗?” 公元9年正月,长安小雪,未央宫瓦沟滴水成线。王嬿缩在椒房寝榻,把铜脚炉蹬到脚跟,仍觉得凉气顺着袜口往上爬。 她守寡一年,朝会常被“太后宜静养”挡在帘后,午后便让宫女去屏风外守着,自己合眼偷片刻盹。 帘下梭梭响,一个青袍内侍挨地皮滑进来,跪得极低,声音贴地:“奉诏请脉。”王嬿懒得睁眼,把手腕递出帐口。 指尖骤被攥住的刹那,王嬿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。那手掌粗糙,带着常年握剑的厚茧,哪里是医官该有的手!她猛地睁眼,帐幔缝隙里,正撞见一张贼眉鼠眼的脸——是王莽身边最得用的内侍王盛! 一股怒火直窜头顶,王嬿猛地抽回手,力道大得带翻了榻边的茶盏。青瓷碎片溅在青砖上,脆响惊得殿外的宫女簌簌发抖,却没一个人敢进来。她太清楚了,这些人早被王莽换成了自己的耳目,她的椒房殿,早成了一座镀金的囚笼。 “放肆!”王嬿的声音发颤,一半是气,一半是怕。她守寡一年,守的不只是汉平帝的灵位,更是汉室最后的体面。王莽是她的生父,可这个父亲,亲手毒死了她的丈夫,又逼着她以太后之尊,为他篡汉建新铺路。 王盛却丝毫不惧,反而凑得更近,声音压得像蛇信子:“太后何必动怒?陛下说了,您年纪轻轻,何苦守着这空殿活受罪?” “陛下”二字,像针一样扎进王嬿的耳朵。这时候的天下,哪里还有汉家天子?公元9年的正月,王莽早已撕下了忠臣的面具,逼着孺子婴禅位,自己登基称帝,国号“新”。她这个太后,不过是他用来装点门面的摆设,是他向天下人证明“新朝得位正”的工具。 王嬿死死咬着嘴唇,尝到了血腥味。她想起一年前,汉平帝病重时,王莽亲自端来的药汤。她那时还傻傻地以为,父亲是真心疼惜女婿,直到平帝喝下药汤后七窍流血,她才明白,这世上最狠的刀,往往藏在亲人的笑脸里。 她是王莽的女儿,却也是汉室的皇后、太后。这双重身份,把她架在了火上烤。王莽要她配合,要她下旨“劝进”,要她做新朝的“安国太后”,可她偏不。她把自己关在椒房殿里,不接旨,不见人,像一株枯死的梅树,守着汉室的残雪。 王盛见她不说话,又阴恻恻地开口:“太后若是识相,陛下自然不会亏待您。若是执意拧着来……这未央宫的冷宫,可比椒房殿冷清多了。” 这话里的威胁,明晃晃地摆在台面上。王嬿抬起头,看向帐外的天空。雪还在下,未央宫的琉璃瓦,在雪中泛着冷光。她忽然笑了,笑得眼泪都掉了下来。她笑自己天真,以为守着寡就能守住气节;笑王莽虚伪,以为靠着威逼利诱就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;更笑这乱世,女子的命运,从来都是任人摆布的棋子。 她猛地抓起榻边的玉簪,抵在自己的脖颈上。冰冷的玉质贴着皮肤,激得她打了个寒颤,却也让她的脑子清醒了几分。 “回去告诉你的陛下,”王嬿的声音不大,却字字清晰,“我王嬿生是汉家人,死是汉家鬼。想让我做新朝的官,做梦!” 王盛的脸色瞬间变了。他没想到这个看似柔弱的太后,竟然有这般烈性。他不敢真的逼死她——毕竟,王莽还要靠着她的身份,粉饰自己的“仁孝”呢。 王盛悻悻地收回手,弯腰捡起地上的青瓷碎片,弓着身子退了出去。帘帐被风掀开的瞬间,王嬿看见殿外的雪地里,站着几个手持兵刃的侍卫。 原来,他早就防着她了。 王嬿瘫坐在榻上,把脸埋进锦被里,哭得撕心裂肺。铜脚炉里的炭火早已熄灭,凉气从脚底蔓延到心口。她知道,从今往后,她的日子只会更难。王莽不会放过她,新朝的官员会嘲讽她,就连汉室的旧臣,也会怨她是“叛贼之女”。 可她不后悔。她是太后,是汉家的太后。哪怕汉室已经倾颓,她也要守住这最后一丝风骨。这不是固执,是一个女子,在乱世里能做的,最卑微也最骄傲的反抗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