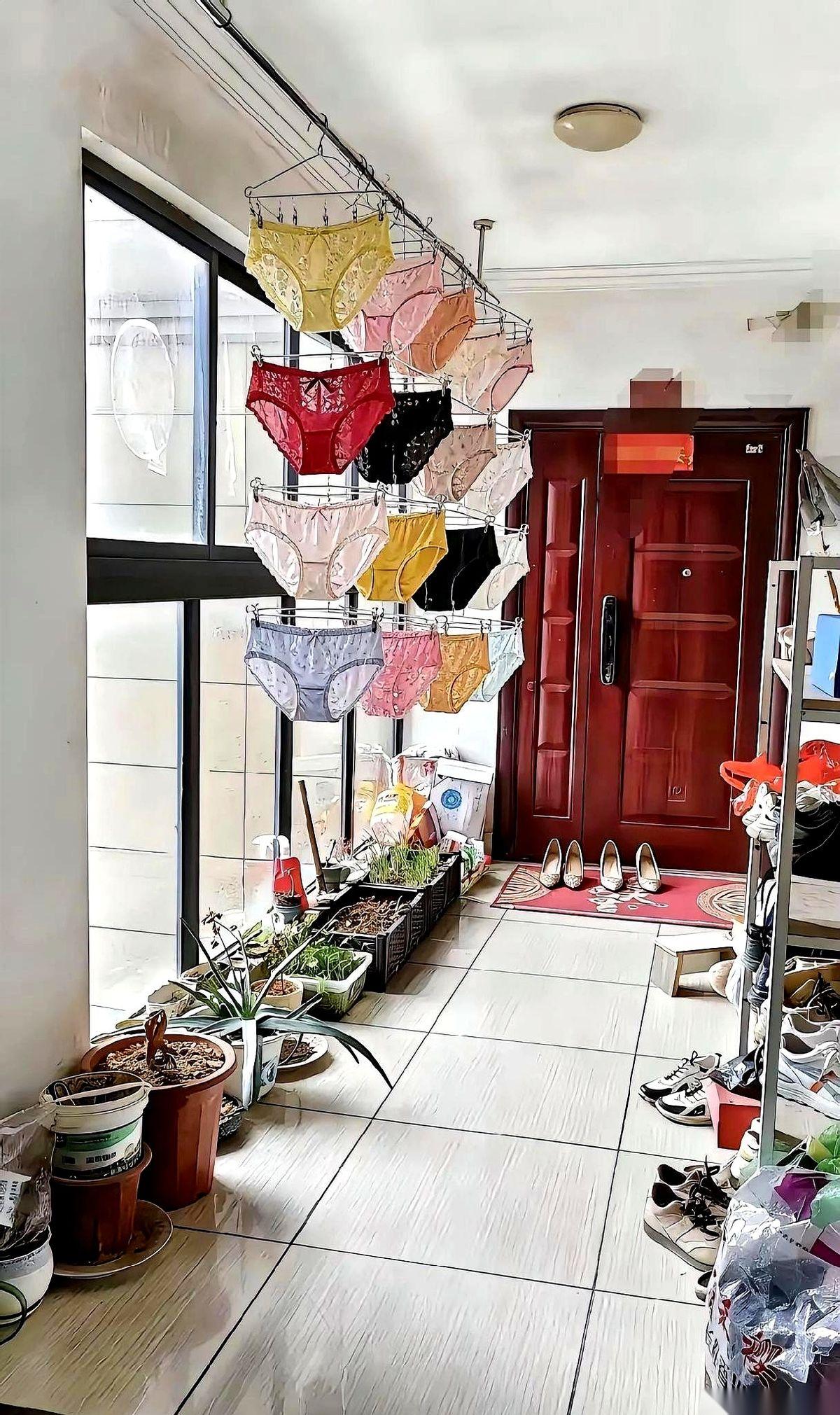9年,厂里分房,我工龄不够。师父说他有办法,带我去见后勤科科长。科长翘着二郎腿坐在藤椅上,说现在只有一个名额,但有三户人家等着:一户是双职工,带个三岁孩子挤宿舍;一户是老技工,祖孙三代八口人住两间平房;还有一户是丧偶的女焊工,带着瘫痪婆婆。科长弹了弹烟灰:“小赵,你挑。”我搓了搓手心,手心全是汗,黏糊糊的,跟抹了层胶水似的。 暖水瓶掉了漆的地方有点锈,像块没洗干净的疤。我盯着那疤,脑子里突然蹦出前儿个在车间楼道看见的场景——张师傅家的豆豆裹着件小棉袄,小脸烧得通红,李娟蹲在地上抱着他,后背一抽一抽的。宿舍楼道风大,窗户缝漏风,豆豆咳一声,李娟就跟着抖一下,嘴里念叨“再坚持会儿,爸下班就带你去医院”。那会儿我还想,这宿舍是真没法住。 “刘科长,”我嗓子有点干,咽了口唾沫,“我觉得……张师傅家更该要这房。” 科长“嗯?”了一声,藤椅“嘎吱”响,他往前倾了倾,烟灰掉在裤子上,慌忙用手拍:“你再说一遍?老周师傅可是八级钳工,当年给进口机床挫零件,眼睛闭着都比尺子准;王姐一个人扛着瘫婆婆,天天背楼上楼下……” “我知道,”我打断他,声音发飘,“可豆豆才三岁,发着烧蹲楼道里哭,我瞅着……心里不得劲。老周师傅家孩子大了,王姐……王姐可能再熬熬……”越说越没底气,手心汗顺着指缝往下滴。 科长没说话,就那么看着我,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外机“嗡嗡”响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突然笑了,从抽屉摸出烟盒,抖出根烟:“行吧,就张师傅。”拿起电话拨分房办,“把那套一楼的,记到装配车间张强名下。” 下楼时腿有点软,师父蹲在花坛边抽烟,见我过来,把烟屁股摁灭在土里:“选的谁?” “张师傅家。”我踢着脚下的小石子,石子滚到冬青丛里。 师父没说话,盯着远处围墙外的老槐树看了半天,才站起来拍我肩膀:“回家吧,你师母炖了萝卜汤。” 后来张师傅搬新家那天,非拉我去吃饭。豆豆穿着新棉袄,在屋里跑来跑去,脸蛋红扑扑的,抱着个苹果塞我手里:“赵叔叔,甜!”我咬了口,确实甜。 前几天在菜市场碰见王姐,她背着婆婆去买药,婆婆在背上哼哼,王姐一步一步挪得慢,额头上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淌。我赶紧把头扭过去,假装看旁边卖白菜的,耳朵里却听见王姐喘着气说:“妈,快到了,再忍忍……” 风从菜市场棚顶的破洞钻进来,吹得我脖子凉飕飕的。
9年,厂里分房,我工龄不够。师父说他有办法,带我去见后勤科科长。科长翘着二郎腿坐
嘉虹星星
2026-01-11 18:10:06
0
阅读:4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