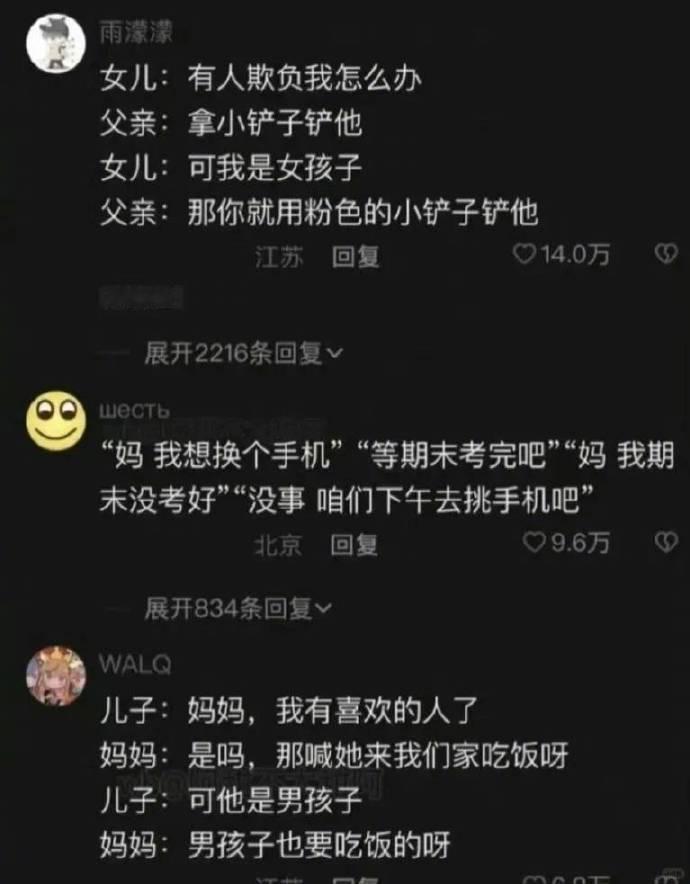1964年,一个知青在看钱学森的论文时,发现方程推导错了,就给钱学森写信,谁知钱学森不仅回了信,还说:“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!” 写信的人叫郝天护。 清华大学毕业,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,抬眼是黄土风沙,低头是实验和教材。 条件不富裕,苦是真的苦,可他心里有个小爱好没丢,订资料、翻论文、关注学术动态,那点精神头,是他在艰苦岁月里给自己留的一点甜头。 上大学那会儿,他在清华听过钱学森做学术报告。讲的是力学里的大问题,推导写得密密麻麻,黑板擦了一遍又一遍。那天之后,钱学森在他心里,就不只是书上的名字,而像立在讲台上的一盏灯。 很多年过去,人走到新疆,讲台看不见了,灯印在心里还在亮。 有一天,他手里捧着钱学森发表的一篇论文,一行一行往下看。 平时看这种文章,更多是学个思路、揣摩个方法。那天眼睛往下一滑,落在一个方程上,心里突然打了个结。推导前后的逻辑在脑子里过了一圈,越想越不对劲,像哪颗螺丝拧反了。 郝天护又重新算了一遍,纸上写满数字,结论还在提醒他,这里有问题。 问题找到了,人却有点犯怵。 对面的名字是钱学森,不是普通教师。 写信指出错误,说轻巧一点叫严谨,说难听一点,容易被人看成“不知天高地厚”。 他心里打鼓,信纸铺开又叠起,字写了又划掉。犹豫了很久,还是把自己的推导过程写清楚,语气尽量放得客气,按着日期写上“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”,把信投进了邮筒。 信抵达北京时,郝天护已经回到自己的农学院,继续忙日常工作。 那边的信封被拆开,纸张摊在桌上,一个熟悉的名字跳进视线,后面跟着一段客气又带点“犯疑”的内容。钱学森看完,有点惊讶。 一个边疆青年,说他的方程推导错了,这话换个环境,很容易被当成笑谈。 纸不能只看文字。 钱学森把自己那篇论文找出来,翻到相关的地方,对着信里的提示,一步一步重算。 推导过程像一条长链子,每一环都要过手,一环一环看下去,精力要集中,心态也要稳。等他把那一节算完,心里已经有数,这条方程推导的确存在问题,错误不算惊天,但确实是错。 人的反应在这时就分出了层次。有的人会本能护住面子,觉得一旦承认错误,权威光环就得暗一截。也有的人干脆当没看见,让错误被时间盖过去。 钱学森没有沿着这两条路走下去。 他心里对这件事的排序很简单:谁说的不要紧,算式对不对才要紧。 所以桌上又铺开一张信纸,笔尖落下去,先写感谢。 感谢这位青年认真阅读论文,也感谢他指出方程中的错误。这样的感谢不算花架子,是写给问题本身的,也是写给那份较真的劲儿。 接着,他提出一个请求,请郝天护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,再寄来一份。 几千公里外,郝天护收到回信,心里那股惊讶,说什么都嫌淡。 他本来只是抱着“说一声就好”的想法,把问题写出去,谁知等来了亲笔回信,还有一份这样的要求。 当初写信带着不安,这会儿再看,自信多了一点,也踏实多了一分。 他按信里的意思,把自己的推导和理解重新梳理,用尽量简洁的方式写成文章,大约七百字,仔细誊抄好寄出。 七百字在很多人眼里不算长篇,在学术刊物上却要经得起挑剔的目光。 钱学森看完这篇稿子,觉得内容扎实,推导清楚,就把它推荐给《力学学报》。这一步,分量就变了。原本只是一封来往书信里的纠错,如今被推到公开刊物上,让更多同行看到,让问题在阳光下被讨论。 文章发表后,边疆那头的青年受到了很大的鼓舞。 日子往前翻。 一九七八年,全国的气息都在变。郝天护回到母校清华,参加研究生考试,重新走进熟悉的校园。在这里,他不再只是讲堂下面的听众,而是要在实验室里、在论文里,和更多学者面对面较劲。之后的路越走越专,他在固体力学领域扎下根,成为这方面的专家,也成了习惯待在一线的科研人员。 有人回头看,会把一九七八年当作一个转折点。 其实那条路早在一九六四年的那封信里,就已经拐了个方向。 一边是艰苦环境里的坚持,一边是认真较真、不怕得罪人的劲,再加上权威的开阔和严谨,几样东西凑在一起,把一个“普通青年”的轨迹推得更长更远。 钱学森在这件小事里的选择,也留下一种尺度。 他没有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,不以名气压人,不因为对方“名不见经传”就一笑了之。他用核算事实、承认错误、邀请发表的方式,把“权威”的帽子放到一边,把“科学”三个字摆到桌面中央。这样的态度,比再多的口头宣讲都更有说服力。 郝天护那边,从敬仰到敢提意见,从鼓起勇气写信,到按要求写出七百字的文章,又在多年后回到清华深造,这一连串动作背后,站着一种很朴素的信念。 一封写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的信,从新疆走到北京,从青年走到大家,把两代人的名字写在同一个算式边上。 纸上那句“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”,落墨不重,却把“治学严谨”四个字刻得很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