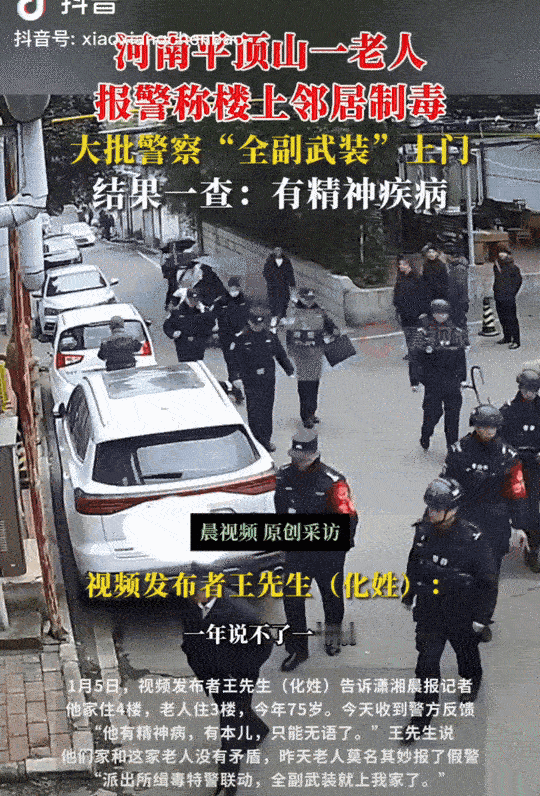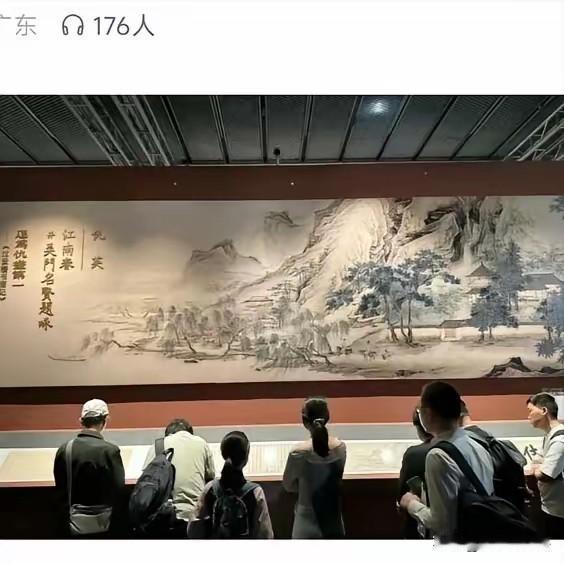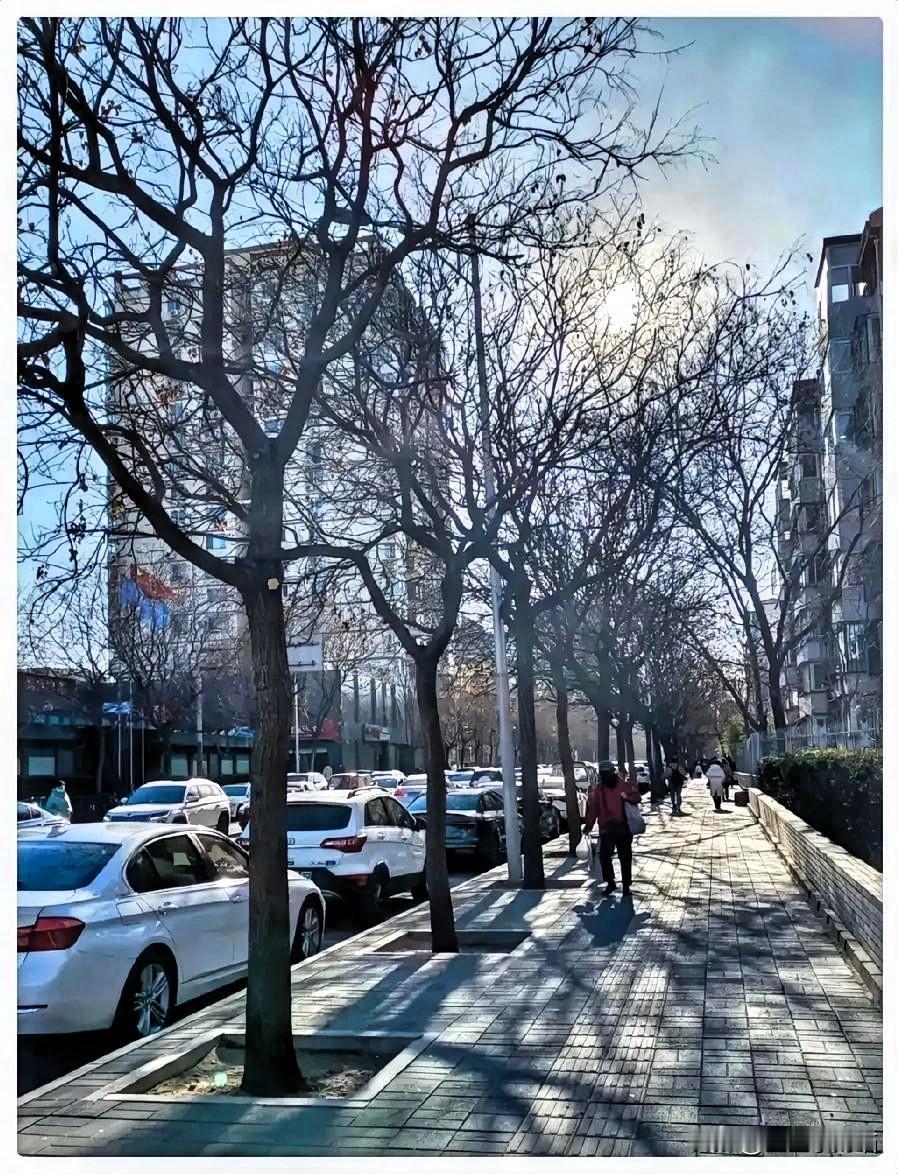"七二年以前,一个公社一个武装部,工作人员不超过5人,一辆机普车,一个大队一部手摇式转接电话机,晚上照明用的煤油,猪肉凭票五六毛钱一斤,穿衣每人1丈5尺布票,一个馒头3两粮票7分钱,没有自行车,土地集体所有,挣工分,交公粮,一个大队一个卫生所,有病3、2毛钱的药片一吃就好,基本上不生病。 这些零碎的记忆,是父亲坐在老藤椅上,就着夕阳说给我听的。他说这话时,手里总摩挲着那个掉了漆的搪瓷缸,缸子上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字样早已模糊,倒是缸底那个小豁口,摸起来还硌手——那是五十年前抗旱时,他从坡上摔下来磕的。 父亲说那年夏天邪乎,三个月没正经下雨,地里的玉米叶子卷得像鞭炮,队长急得嘴上燎起一串泡。全队男劳力都去村西的机井打水,父亲年轻,被派去给大家送水。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挑着两个木桶去井边接水,再用搪瓷缸给排队浇水的人舀水喝。那天日头毒得像要把地烤裂,他挑着两桶水往坡上爬,扁担压得肩膀生疼,每走一步都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气声,搪瓷缸在桶边晃悠,里面的凉白开跟着荡出小水花。 爬到半坡时,脚下一滑,他整个人往前扑,下意识用胳膊去撑地,搪瓷缸“哐当”一声掉在石头上,磕出个豁口。水洒了大半,他顾不上疼,爬起来就去捡缸子,手指被豁口划了道血口子,血珠滴在缸沿上,倒像给“农业学大寨”那几个字添了点红。旁边的老支书看见了,过来拍他后背:“傻小子,命重要还是缸重要?”他咧着嘴笑,把缸子往怀里揣:“这缸子跟我半年了,比锄头还亲。” 后来还是老支书把他拽到树荫下,用自己的汗巾给他包手,又从兜里摸出半块干硬的玉米饼,塞他手里:“吃点垫垫,别中暑了。”那天下午,父亲到底没扛住,头晕眼花地栽倒在田埂上,是三个社员轮流背他去的卫生所。王大夫给开了两毛钱的藿香正气片,又让他趴在长凳上,用酒精擦脊梁骨,凉丝丝的,他迷迷糊糊听见王大夫跟支书说:“这娃是累着了,让他歇两天吧。” 可第二天一早,父亲又挑着水桶出现在井边,搪瓷缸豁口朝外,装在桶边的网兜里晃悠。老支书瞪他:“不要命了?”他嘿嘿笑:“地里等着水呢,我歇了,大家就得多受累。”那天收工时,队长在全队面前表扬他,说他那豁口缸子就是“艰苦奋斗”的记号,还奖励了他两分工。 现在父亲用这搪瓷缸泡花茶,豁口朝外,说这样不硌手。茶叶在热水里舒展,他盯着水面上的茶梗,慢悠悠说:“你说那时候累不累?累啊,可看着大家喝着水又埋头干活的样子,心里就跟揣了个热炭似的,踏实。现在日子过好了,喝的茶比那时候的凉白开金贵,可有时候我端着这缸子,还能闻见当年井边的土腥味,听见大家抢着舀水时的笑闹声。”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,搪瓷缸里的茶水泛着琥珀色的光。我突然觉得,那豁口不是磕坏了缸子,是给日子刻了个记号——记着那年夏天的汗,记着互相搭把手的暖,记着人心里那点不肯认输的劲儿。日子是往前走了,可那些记号里藏着的热乎气,还在呢。
一个女生放假后偷偷坐高铁回广东家里,想给爸妈个惊喜。趁家里没人溜进去,她躲在大门
【49评论】【157点赞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