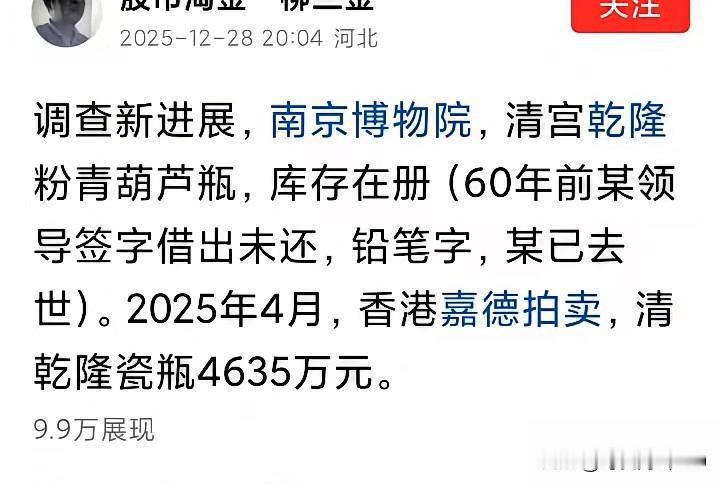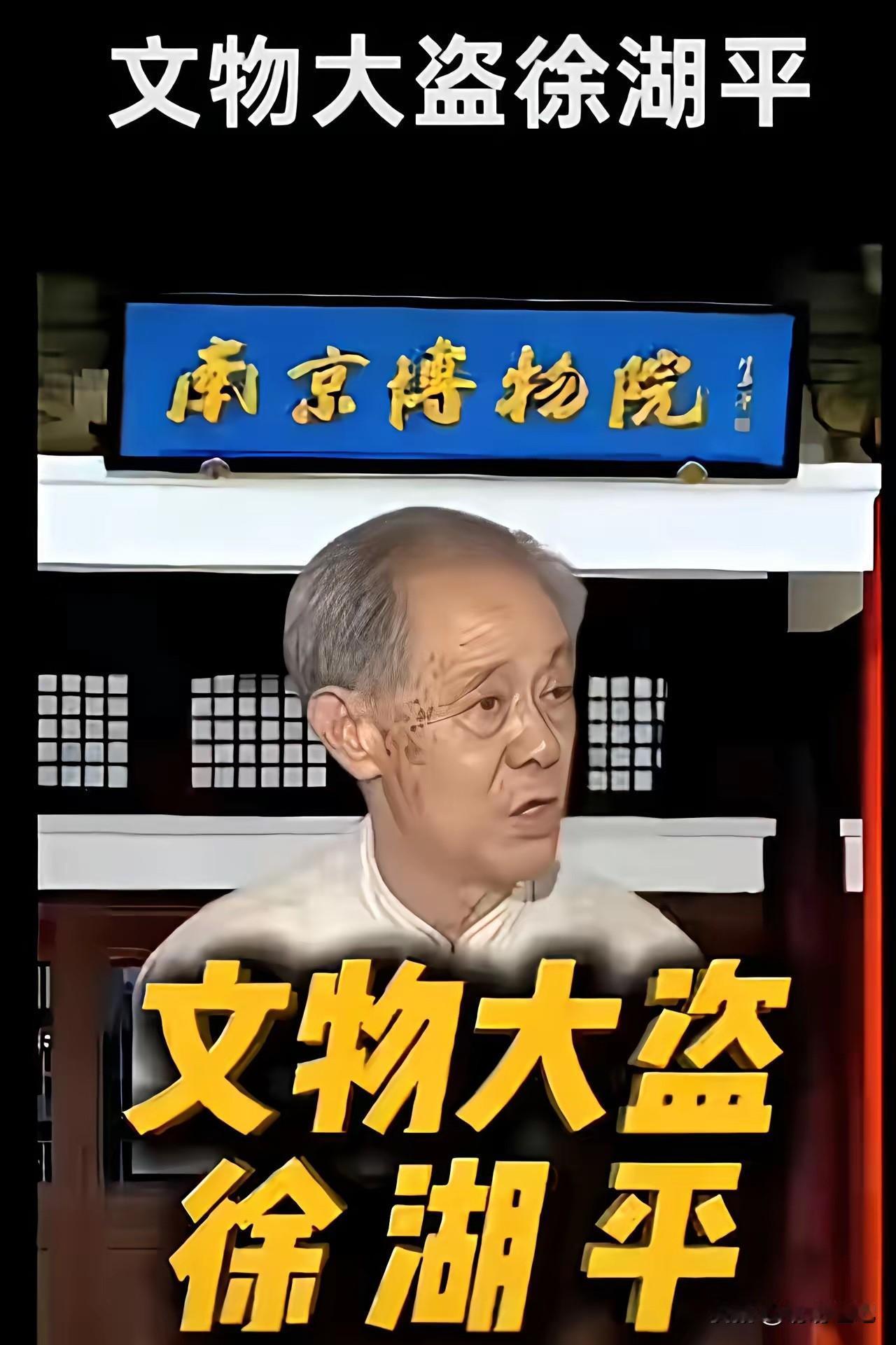1952年,北大一教授,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,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,却忽然脸色大变,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,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。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,一幅古画静静陈列。 编号1101的标签旁,“一级国宝”四个大字格外醒目。 这是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御容像,元代宫廷原作。 很少有人知道,它的现世,藏着一段跨越数百年的历史纠葛。 画中人物头戴七褶白貂帽,身着左衽锦袍。 这看似简单的服饰,藏着元朝的等级礼制密码。 七褶狐帽并非寻常饰物,是蒙古大汗的专属礼帽。 以极北之地的白貂皮缝制,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。 而左衽衣袍,是蒙古民族的传统服饰标识。 与中原汉人的右衽习俗迥异,体现着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。 这种服饰细节的精准还原,只有宫廷画师能做到。 回溯到1278年的元大都,宫廷画院灯火通明。 忽必烈正下令画师绘制先祖御容,以供奉太庙。 这在元朝有着严格的礼制规定,御容绘制需遵循“神似为先”。 画师需参考皇室珍藏的先祖画像底本,不得随意创作。 当时的元朝宫廷画院,汇聚了汉、蒙、藏等各族画师。 他们分工协作,有人勾勒轮廓,有人渲染色彩。 所用的桑皮纸,是元代专门为宫廷特制的书画用纸。 纸张经过多道工序处理,坚韧耐存,适合长期供奉。 画卷角落的“大元内府”印章,更是宫廷藏品的铁证。 这方朱红印章,是元朝内府收藏的专属标识。 只有经过皇帝审定的珍贵文物,才能加盖此章。 按照元朝礼制,御容像需供奉于太庙,严禁私人收藏。 这幅成吉思汗御容像,为何会流出宫廷? 历史记载,元朝末年,战乱四起,元大都被攻破。 宫廷藏品遭到大肆劫掠,不少国宝就此流落民间。 这幅御容像或许就是在此时,逃离了宫廷的禁锢。 此后数百年,它如同人间蒸发,再无记载。 直到清末民初,这幅画才再次出现在历史视野中。 当时北洋军阀陈宦担任蒙疆经略使,负责边疆事务。 他与蒙古亲王交往密切,这幅画被当作厚礼相赠。 这背后,是当时蒙汉交流的历史缩影。 民国初年,中央政府与蒙古地方保持着紧密联系。 贵重文物的相互馈赠,是维系关系的重要方式。 陈宦将这幅画视为珍宝,小心收藏于家中。 可世事无常,陈家后来家道中落,藏品逐渐散佚。 后人不知这幅画的珍贵,只当是普通旧画。 1952年深秋,北京西单的地摊上,这幅国宝重现。 崔月荣守着几卷蒙尘的字画,神色憔悴。 她是陈宦的后人,为糊口只能变卖家中旧物。 史树青的出现,成为了国宝命运的转折点。 当时他刚结束北大的教学工作,习惯性地逛地摊。 多年浸润琉璃厂的经历,让他对古物有着敏锐感知。 他强压着内心的激动,不动声色地拿起画轴。 画中人物的服饰细节,与他研究过的元代史料完全吻合。 “这画怎么卖?”他刻意让语气显得随意。 “您看着给吧。”崔月荣的回应带着几分疲惫。 史树青掏出3块钱递过去,交易就此完成。 这3块钱在当时能买16斤白面,是普通工人半月工资。 但对史树青而言,这是挽救国宝的关键一步。 他抱着画轴匆匆回家,连夜展开细致研究。 “大元内府”印章的发现,让他确定这是宫廷藏品。 可他并未急于定论,深知文物鉴定需严谨。 他带着画作拜访了张珩、启功等鉴定大家。 几位专家反复研究,结合元代史料展开论证。 最终确认,这幅画正是忽必烈时期的宫廷御容原作。 它比台北故宫的明代摹本早近200年,极具史料价值。 这幅画的发现,填补了元代御容研究的空白。 也为研究成吉思汗的真实形象提供了直接依据。 要知道,成吉思汗生前有遗训,不许人为自己画像。 市面上流传的多是后人想象之作,可信度极低。 1953年,史树青做出了无偿捐赠的决定。 他说:“国宝属于民族,理应回归国家收藏。” 这并非他第一次捐赠文物,早在15岁时就有先例。 当时他花两毛钱淘到丘逢甲书法真迹,直接捐给国家。 这份对文物的敬畏与守护,贯穿了他的一生。 此后多年,史树青始终致力于文物保护事业。 他凭借专业学识,从地摊上挽救了无数珍贵文物。 每一件文物的背后,他都会深入挖掘历史故事。 让这些沉默的古物,重新诉说过往的历史。 晚年的史树青,将鉴定经验整理成书。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,培养更多文物保护人才。 他常说:“文物是历史的见证,每一件都值得珍视。” 2007年,史树青在北京逝世,享年86岁。 而那幅成吉思汗御容像,依旧在国博静静陈列。 那些沉默的古物背后,藏着民族的记忆与根脉。 守护它们,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文化。 信源:新华网——史树青为国家“捡漏儿” 鉴定国宝的“国宝”(图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