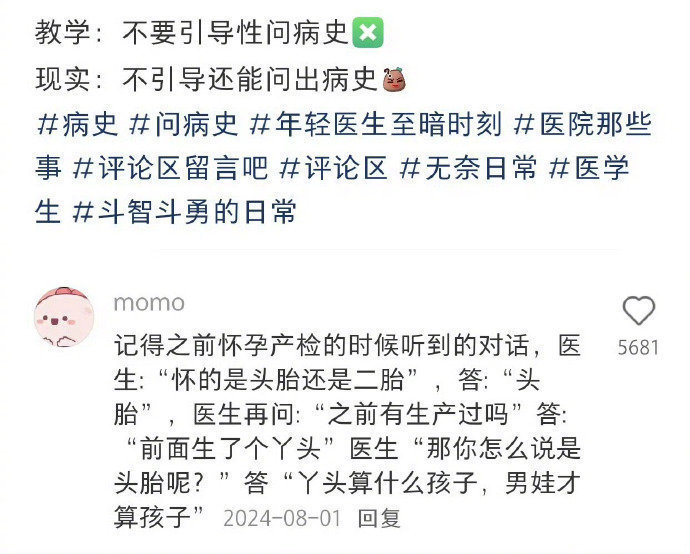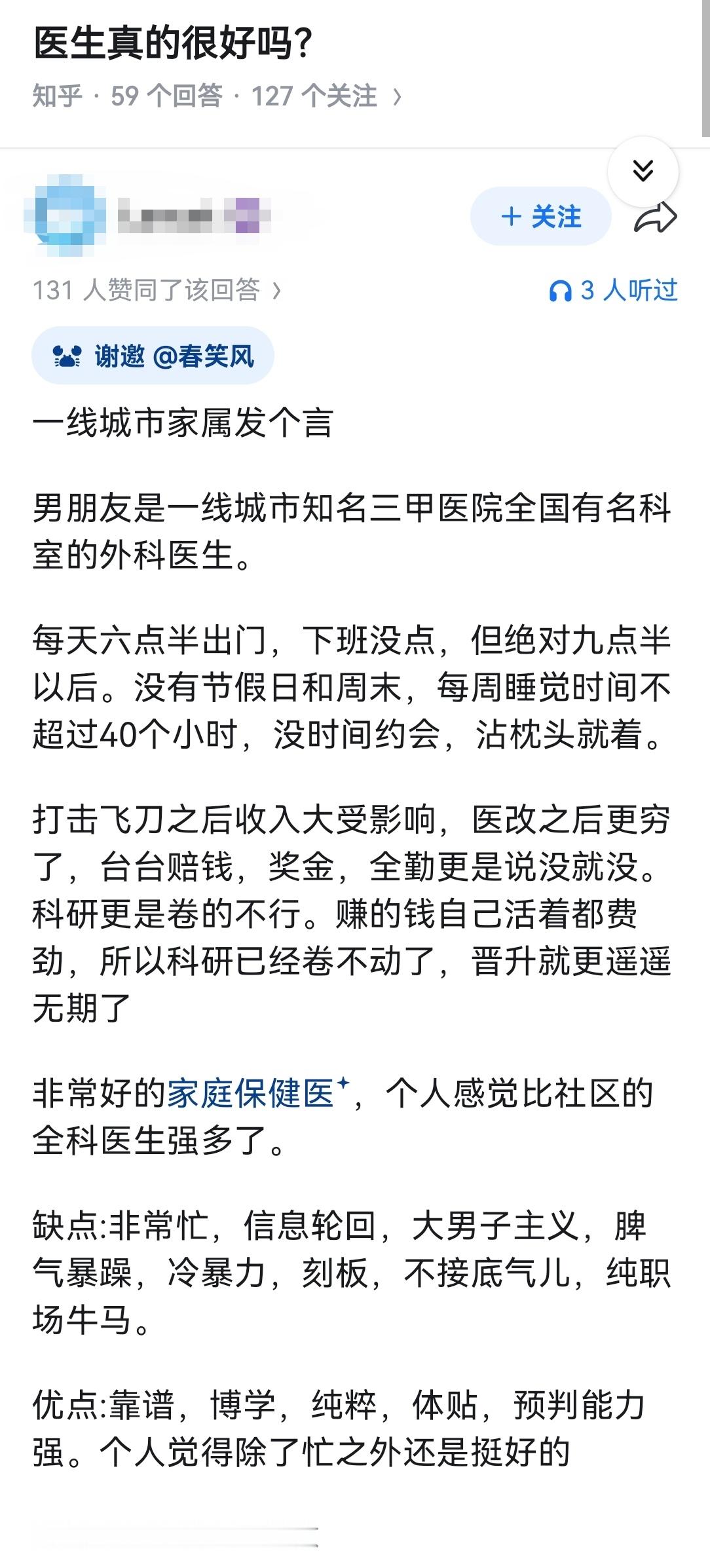[微风]1982年6月16日,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,结果震惊发现,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,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,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。 早在四个月前,那时候的罗健夫,已经被诊断为“低分化恶性淋巴瘤”晚期,这种绝症带来的疼痛足以摧毁人的理智。 医生和护士不止一次拿着镇痛剂想要帮他解脱,却一次次被他那只颤抖的手挡了回去,他拒绝注射吗啡类药物,理由听起来近乎“残酷”:“这东西打多了刺激神经,会让脑子变木。” 在这具几近报废的身体里,唯一还没被癌细胞吞噬的,只剩下那个还在高速运转的大脑,他不敢睡,更不敢糊涂,因为图形发生器的III型设计图上,还有几个关键的电控逻辑没跟同事交待清楚。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病房成了他的临时教研室,哪怕只能用一只手死死顶着剧痛的胸口,罗健夫的另一只手还要在图纸上比划,从设计逻辑到调制细节,这一讲,就是两个多小时。 这种“用命换数据”的偏执,其实早在13年前那个搬迁的年份里就埋下了伏笔。 1969年,为了国家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,罗健夫的单位从北京迁往陕西临潼,当时摆在案头的是一道几乎无解的死命令:研制图形发生器。 这是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“母机”,没有它,造芯就是空谈,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这技术被国外封锁得连张纸片都漏不进来,只能两眼一抹黑地硬搞。 这一年,罗健夫34岁,原本是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的高材生,现在却要他去搞电子线路、精密机械和自动化控制。 这意味着,过去十几年的专业积累归了零,他得像个新兵一样,把自己重新扔进完全陌生的知识荒原,于是,在那几年的西安街头,出现了一个奇怪的“魔怔人”。 公交车上,别的乘客都在闲聊或者看风景,只有他,像尊雕塑一样死死盯着膝盖上的专业书,有好几次,车都到了终点站掉头往回开了,售票员还得扯着嗓子喊,才能把他从复杂的线路图中“喊”回现实。 在那些为了赶进度的夜晚,实验室地板就是他的床,干硬的冷馒头就是他的餐点,同事眼里的他,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,比书本里那个叫“保尔”的钢铁战士还要纯粹。 整整4000多个日夜的煎熬,最终换来了中国电子工业的破局——1972年,第一台图形发生器问世;三年后,更先进的Ⅱ型机横空出世,填补了国内的空白。 但奇怪的是,当荣誉真的像雪片一样飞来时,那个为了科研敢把命豁出去的人,却突然“隐身”了。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,那是科研界顶级的荣耀,但在申报成果的名单上,罗健夫执意把自己的名字挪到了最后一位;单位好不容易盼来了那次二十年一遇的涨工资机会,他让了;组织给的3000元巨额奖金,他分文不取;哪怕是大家都眼馋的出国考察名额,他也拱手让人。 面对周围人的不解,他只是淡淡地抛出了一句甚至听起来有些傻气的话:“我就一句话,努力切勿人后,成功不必在我。”这不是客套,在这个倔强的湖南人眼里,没有什么比那张图纸的完美更重要,如果有,那就是把更宝贵的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。 甚至在临终前,当有人想方设法给他弄来昂贵的进口特效药时,他依然是摆手:“别浪费在我身上了,给更有希望的病人吧。” 他走得太干净了。除了那个最后时刻强撑着身体缴纳的党费,和那两个把自己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的遗愿,他似乎什么都没给自己留下。 医生们缝合遗体时落下的眼泪,不只是因为看见了那个骇人的肿瘤,更是因为看见了一个纯粹灵魂的实体化。 在那个中国航天和电子工业正如饥似渴需要补课的年代,罗健夫和许许多多像邓稼先、钱学森一样的人,选择把自己活成了一块燃料。 他们当然知道疼,知道苦,但在“国家需要”这四个字面前,个人的痛觉被意志屏蔽了,个人的得失被信仰稀释了。 他到死都把自己当作一台为了国家运转的精密仪器,哪怕零件坏了、线路烧了,也要在彻底停机前,输出最后一个正确的数据。 信源:湖南日报《罗健夫:心中有家国 淡泊且执着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