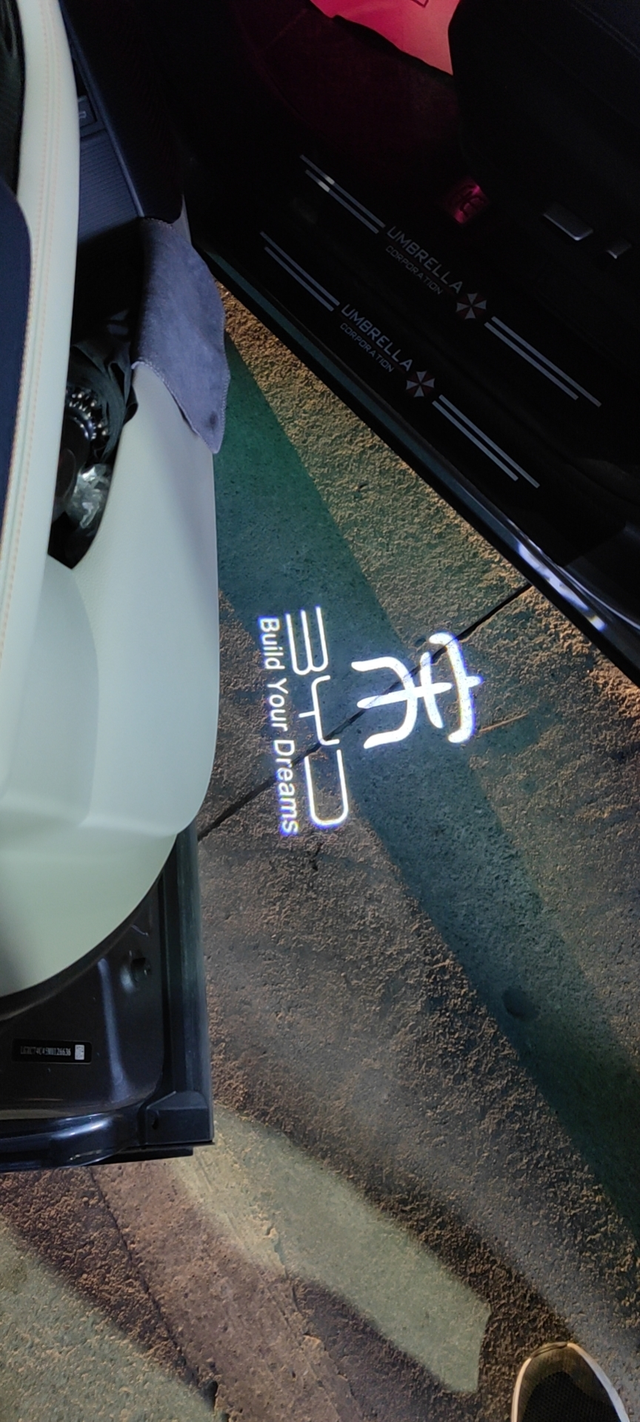昨天在茶馆打牌,我着实被吓得不轻。当时我邻居就坐在我右手边,59岁的年纪,正轮到我来摸牌时,她突然猛地一把攥住我的手,说自己头晕得厉害。她手凉得像冰,脸煞白,嘴唇都没了血色。我赶紧把牌推到一边,扶她往椅子上靠:“老张,你咋了?要不要紧?”旁边打牌的王婶也慌了,摸出手机就想打120,老张却摆摆手,声音虚得很:“别……别麻烦,我兜里有药,速效救心丸。” 昨天下午的茶馆,阳光斜斜地切过牌桌,落在我右手边老张的搪瓷杯上——那杯子掉了块漆,露出里面的白瓷,她总用它泡胖大海,说嗓子不好,得润着。 我们是老邻居了,住对门十年,每周三下午雷打不动来这儿打牌。她59岁,头发染得乌黑,跳广场舞时领舞的架势比小姑娘还精神,谁能想到会出这事儿。 当时我正摸牌,指尖刚碰到那张冰凉的“九条”,右手突然被死死攥住。不是平时开玩笑的力道,是带着点颤抖的、发狠的攥,像生怕我跑了似的。 我低头看她。她的手凉得吓人,不是天气冷的那种凉,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寒气,指甲盖都泛着青;脸上一点血色没有,白得像刚裱好的宣纸,嘴唇抿成一条线,连平时总带着笑的嘴角都往下垮着。 “老张?”我把牌扔回桌上,赶紧扶住她胳膊,“你咋了?头晕?” 旁边王婶眼尖,“哎呀”一声站起来,摸出手机就按“120”,“快!快叫救护车!” 老张却猛地摇头,另一只手胡乱往裤兜里摸,声音虚得像棉花,“别……别叫,我兜里……有药,速效救心丸。” 那一瞬间,桌上的麻将牌还散着,红中绿发在阳光下泛着冷光,而她攥着我的力道却越来越紧,像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似的,让我心里猛地一沉——这哪是平时那个会跟我们抢最后一块酱肘子、跳广场舞非要站C位的老张啊? 王婶已经翻出药瓶,手抖得拧不开盖子,我接过来,倒出几粒棕色的小药丸,塞进她嘴里,又端过她的搪瓷杯,“来,含着,慢慢咽。”她平时喝茶总说“要热乎的才够劲儿”,这会儿杯子里的水却温温的,大概放了有些时候了。 你说人这一辈子,到底是“不麻烦人”重要,还是让在乎的人安心更重要?老张就是太好强,上次她崴了脚,愣是自己一瘸一拐爬五楼,说“儿子上班忙,别让他分心”,结果肿得跟馒头似的,还是我送饭时才发现。 药含下去没半分钟,她的手松了点,脸色也缓过一丝粉,只是说话还不利索,“让……让你们……受惊了。” “说这些干啥!”王婶拍着她后背,“以后兜里揣着药,也得揣着你儿子电话!下次再这样,我们可不管你乐不乐意,直接打给他!” 牌没打完,大家都没心思了。我送老张回家时,她儿子已经从单位赶回来,红着眼圈给我们道谢。老张靠在沙发上,拉着我的手笑,“你看我这身体,关键时候掉链子。” 晚上我翻手机,把她儿子、女儿的电话都设了快捷拨号,又在自己钱包里塞了张纸条,写着家里的门牌号和我的病史——以前总觉得“意外”是别人的故事,可昨天握着老张那双冰凉的手,才明白有些事,真等不及“下次再说”。 今天早上出门,看见老张的搪瓷杯放在她家窗台上,里面换了新的胖大海,在阳光下泡得鼓鼓囊囊的。我朝楼上喊了声“上班去啦”,她推开窗户应着,声音亮堂,“晚上来吃饭啊!我炖了排骨汤!” 牌桌还在茶馆摆着,红中绿发大概还在老位置。只是下次再坐下来,我大概会先看看身边的人,杯子里的水够不够热,兜里的药,是不是真的能救命。
昨天在茶馆打牌,我着实被吓得不轻。当时我邻居就坐在我右手边,59岁的年纪,正轮到
优雅青山
2025-12-17 11:09:11
0
阅读:7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