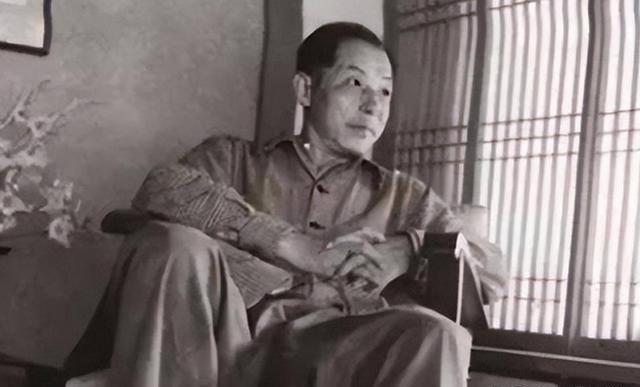陈寅恪最为人诟病的,还不是他被护士指控性骚扰,或者是他超过国家领导人的变态待遇,而是他对于抗战的态度。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发生,吴宓在7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道:
“晚饭后,7一8与陈寅恪散步。寅格谓中国之人,下愚而上诈。此次事变,结果必为屈服。华北与中央皆尤志抵抗。且抵抗必亡国,屈服乃上策。保全华南,悉心备战:将来或可逐渐恢复,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。……战则全局覆没,而中国永亡矣云云。”
两人的关系还不错,因此吴宓没有什么动机给他造个谣写在日记里。
到了7月21日,吴宓又写道:
“惟寅恪仍持前论,一力主和。谓‘战则亡国,和可偏安,徐图恢复。’”
而最直接的证据,是1944年汪精卫嘎了之后,他十分悲痛,立作了一首七律:
七律《阜昌》
甲申冬作时卧成都存仁医院
阜昌天子颇能诗,集选中州未肯遗。
阮瑀多才原不忝,褚渊迟死更堪悲。
千秋读史心难问,一局收枰胜属谁。
世变无穷东海涸,冤禽公案总传疑。
吴宓在1944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这件事:“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,命宓录之,以示(萧)公权”。所以这件事是可以交叉验证的。
那么这首诗啥意思呢?
“阮踽”即阮籍的父亲,是竹林七贤之一。褚渊是南齐尚书。在诗中,他把汪精卫和伪齐刘豫相提并论,以“阜昌天子”比喻汪精卫。意思是汪氏本来是一代大才,但是遭受了“冤禽公案”。
也就是说他觉得汪精卫没啥问题,都是被冤枉了…这就…
所以我觉得把他定义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好像也不算冤枉他吧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