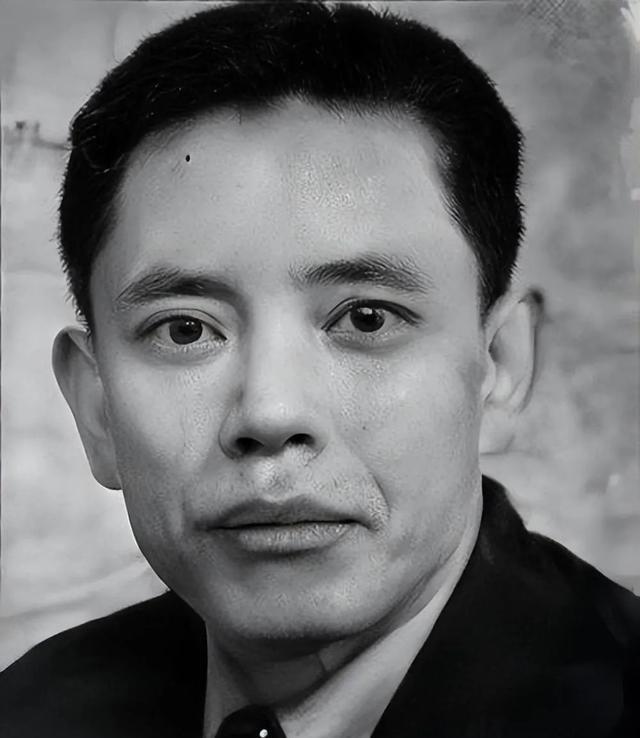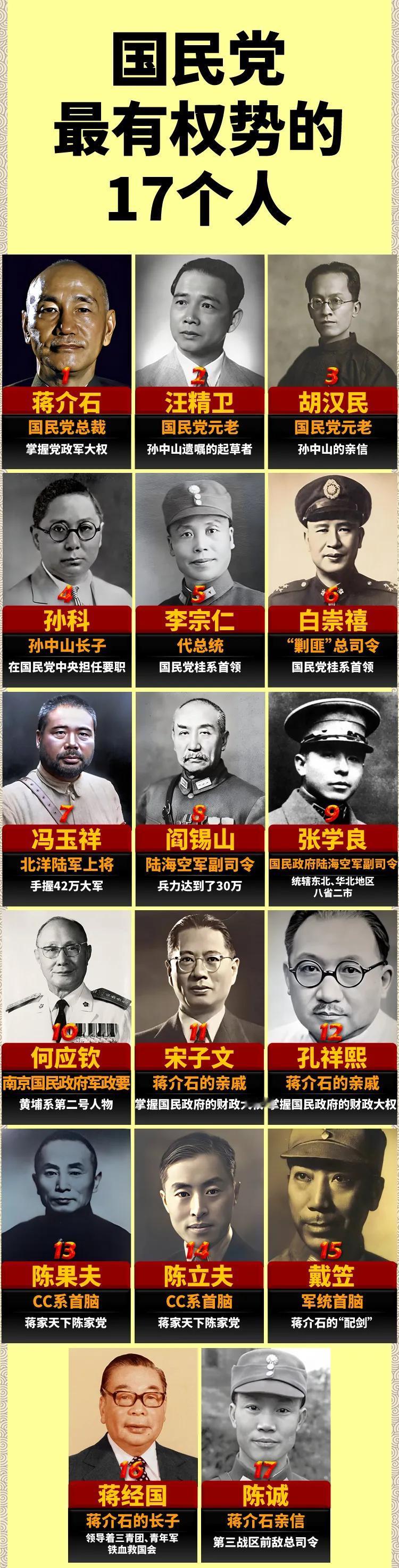1964年,沈醉说:当年徐远举刑讯江姐时,要扒掉江姐的衣裤,沈醉目睹了江姐怒骂徐远举,免遭侮辱的全过程。罗广斌说:江姐的机智、勇敢没写进小说,太可惜。 国民党败局已定时,重庆地下党成了他们最后的猎物。江竹筠被捕后,军统急于挖出川东网络,她成了重点目标。徐远举作为审讯专家,接手这个案子,他的手法一向是先软后硬,挖弱点下手。江竹筠守口如瓶,供词上全是空白,这让他火冒三丈。军统上层施压,要速战速决,他开始用家庭牌,提彭咏梧的死和孩子的孤单,想动摇她。可江竹筠不为所动,坚持原则,这让局面僵持。 沈醉那时是总务处处长,负责监督审讯进度,他去现场查看,就是为了催情报。徐远举的手段越来越露骨,他试图用侮辱方式逼供,目标直指江竹筠的尊严。这不是孤例,军统审讯常带性别暴力,目的是摧毁意志。江竹筠面对这种威胁,没有退缩,她用言语反击,直击徐远举的痛处,骂他不配为人。 徐远举气急败坏,想动手教训,沈醉见状上前干预。他踢了徐远举一脚,不是怜悯,而是觉得这法子太低级,浪费时间。军统要的是情报,不是闹剧,他建议换竹签或吊刑,继续施压。江竹筠就这样避开了最直接的侮辱,审讯草草收场。她被押回牢房,伤痕累累却意志不倒。这件事暴露了特务系统的混乱,徐远举的鲁莽反映出国民党末路的慌乱。 罗广斌后来知道这个细节,从狱友和幸存者口里拼凑。他在写《红岩》时,犹豫要不要加进去,一来敏感,二来怕影响整体基调。小说里江姐的形象更侧重竹签刺指的惨烈,那份用智慧化解危机的勇敢,就这么漏了。他私下跟人说,太可惜了,这才是江竹筠接地气的英雄气质。 军统的审讯逻辑是层层加码,从心理到肉体,徐远举精于此道。他抓准江竹筠的软肋,儿子小小年纪无人照顾,用来劝降。她短暂动摇,但很快稳住阵脚。沈醉的出现是个意外变量,他虽是特务头子,却有自己的算盘,不想让下属坏了规矩。这次干预虽短暂,却改变了进程,江竹筠保住了底线,继续为党保密。 江竹筠转入渣滓洞后,酷刑没停,徐远举换了老虎凳和水牢,她手指肿胀,身体虚弱,却一口咬定不知情。1949年11月27日,国民党制造大屠杀,她和其他烈士一起遇害,年仅29岁。她的死震动了重庆地下党,激励大家坚持到解放。渣滓洞的惨案成了国民党罪行的铁证,解放后,档案公开,世人知晓她的贡献。 沈醉起义后,1950年被捕,关押改造,双手铐链,接受审问。1964年,他在回忆录里写下这段,称江竹筠的反应让他难忘。他获释后,继续披露军统黑幕,写了多本书,1996年在北京去世。 徐远举随国民党退台湾,1950年代还干情报,1970年代退休,1980年代末回重庆,病死时无人问津。他的审讯记录进了战犯档案,交代了多起迫害案。 罗广斌出狱后,埋头写作,《红岩》1961年出版,江竹筠成了不朽符号。他对那段机智勇敢的遗憾,成了私房话,提醒文学要贴近生活。1967年,他因病去世,年42岁,身后作品流传,教育一代代年轻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