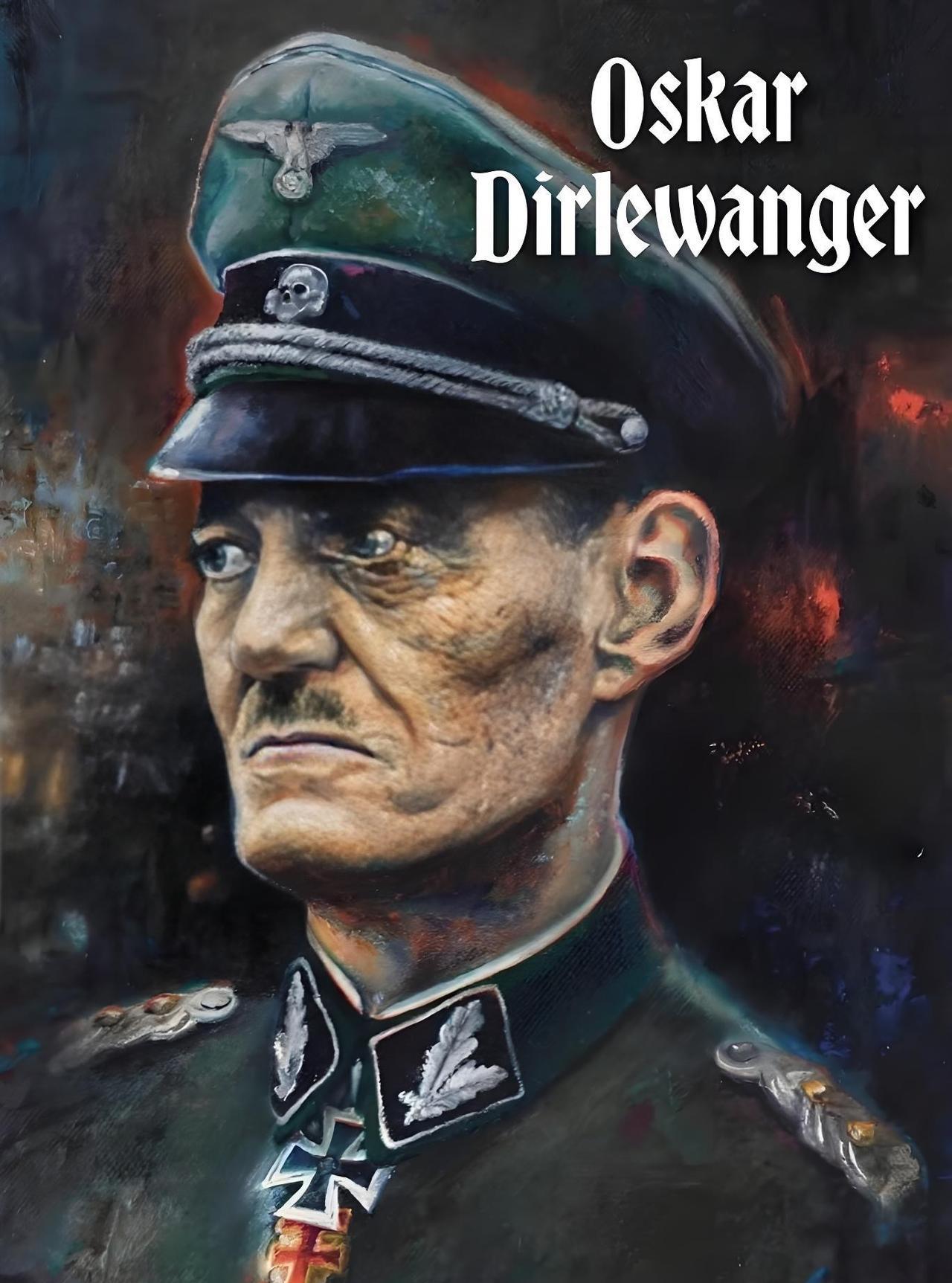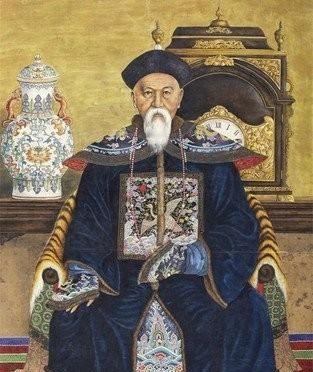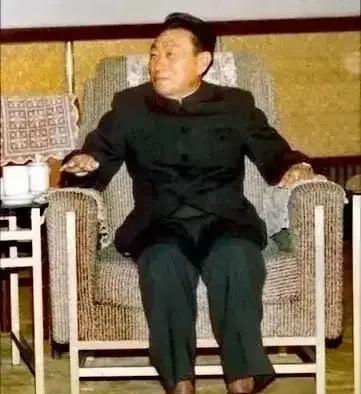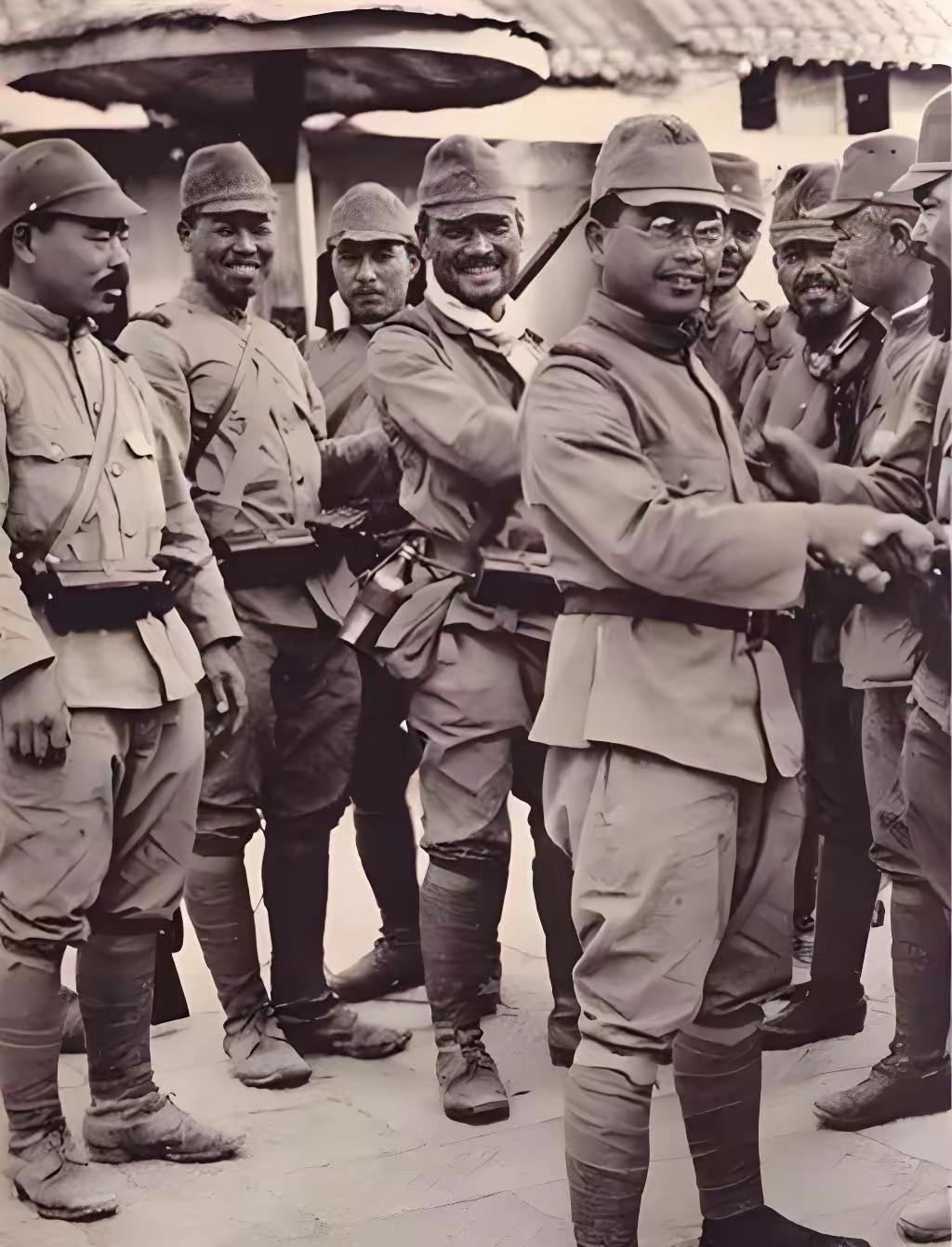1933年,一位叫做莫理循的德国女摄影师,来到北京法源寺游览,当她走到寺里的一座大殿内时,突然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…… 北京大慧寺的银杏叶飘进殿门时,赫达·莫里逊正踮着跛脚凑在莲花座前。 她举着双镜头反光相机,镜头里的千手观音正用11张面孔“盯”着她。 赫达的相机,从十岁就开始陪着她。 1908年出生在出版商家庭的她,偷拿父亲的柯达相机蹲在出版社门口拍行人时,就懂了“镜头能抓住比文字更烫的世界”。 后来她放弃大学学业,成了自由摄影师。 直到1933年,一则广告撞进她的视线。 北京哈同照相馆招女摄影师,要求会三国语言,且是德国兹瓦本人。 赫达把母亲的哭劝和父亲的担忧扔在脑后:“这简直是给我定制的。” 走的时候,她将防身手枪和雨伞丢进北海的浪里,只带了一架双镜头相机和一辆折叠自行车。 那时的中国对德国姑娘来说,是火车转轮船、轮船转马车的遥远旅程。 可赫达不怕。 因为她见过柏林街头的动荡,却更想看看“传说中留着长辫子的国度”。 赫达在北京的十三年,像只停不下的蜂鸟。 她骑着自行车穿遍南锣鼓巷的四合院、前门的绸缎庄、城墙根的茶铺,相机快门声比鸽哨还密。 她的照片里,有拉洋车的车夫擦汗时耷拉的肩膀,有卖花姑娘簪在鬓角的绒花,有老人在槐树下下棋时抖落的棋子。 这些都是即将被战火和时光抹去的“活北京”。 而大慧寺,是她镜头里最“沉”的存在。 这座藏在海淀魏公村的寺庙,大悲宝殿的屋顶已经漏雨,墙面剥落得露出砖坯,可殿内的千手观音却像刚从明代走出来。 木胎沥粉的胎体上,沥粉堆金,28尊胁侍菩萨围在四周,每尊的表情都不一样。 有的像隔壁唠嗑的大娘,有的像庙会上卖糖人的老头,完全没有“神”的距离感。 赫达后来回忆:“我拍了一整天,阳光从藻井漏下来,正好照在观音的嘴角,她像在笑,说‘你看,人间是这样的’。” 她换了三卷胶卷,从特写手部到拍整体组合,连胁侍菩萨袖口的褶皱都没放过。 因为她知道,这些细节随时会消失,重修的工匠可能会“修得更整齐”,却修不掉明代的“烟火气”。 赫达不知道,她拍的这些塑像,是明代雕塑的“漏网之鱼”。 大慧寺的千手观音本是五丈铜佛,日本侵华时被熔了铸炮弹。 后来补塑的木胎观音,工艺虽糙,却保留了明代的“妆玺”传统。 用朱砂、石青、赤金这些天然颜料,没被后来的“重塑金身”破坏。 50年代文物普查时,专家惊觉这些彩塑竟是明代原作! 三次重修都只补彩绘,没动胎体和妆色。 也就是说,赫达拍到的,是六百年前的“原汁原味”。 后来的雕塑专家说:“这种‘不完美’才是最珍贵的,民间工匠没按规矩来,把自己对神的理解揉进了塑像里,你看那尊胁侍菩萨,手里拿着个世俗的布包,像刚从家里出来赶庙会的样子。” 而赫达的照片,正好把这个“不完美”冻成了永恒。 1946年赫达回德国时,带了几百卷胶卷,取名《北京的面孔》。 她或许连自己都没想到,这些黑白照片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中国文化的“坐标”。 如今的大慧寺,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,殿内的千手观音依然立在那里,28尊胁侍菩萨的表情和赫达拍的一模一样。 游客举着手机拍照,会说“这观音真灵”,却不知道,他们的镜头里,藏着赫达的“坚持”,她用胶卷替老北京“抗”住了时间。 赫达的相机早不在了,可她的照片还在。 或许有些人会问:“这些照片有什么用?” 其实,答案藏在观音的微笑里。 因为,文化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,是有人用生命去记录、去保存的“活的东西”。 1933年的那个秋天,赫达按下的不是快门,是“挽留”。 主要信源:(百度百科——洋镜头里的北京(赫达·莫里逊赫达·莫..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