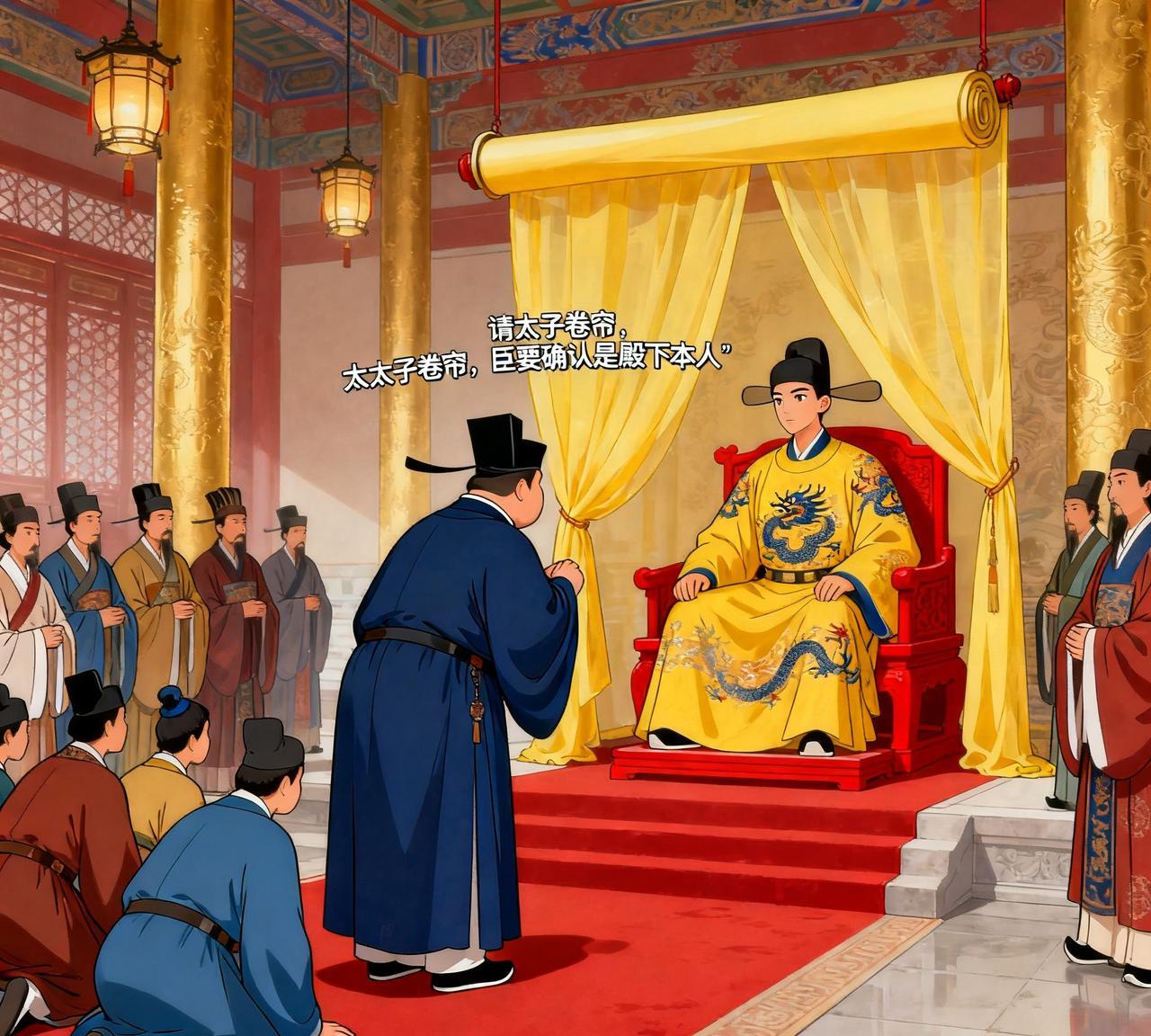1723年,刚登基几个月的雍正,走进户部银库,掀开封条。他眯着眼扫了一圈,脸色当场拉下来。堂堂几亿人的大清帝国,库银只剩区区800万两。雍正没发怒,也没说话,转身出门,一言不发地回宫。这一刻,雍正下定决心:必须动刀子了。 雍正元年的冬天,京城冷得邪乎。 刚登基几个月的皇帝雍正,坐在养心殿的暖阁里,却觉得心里头比外头还冷。他面前摊着户部送来的账本,上面的数字刺眼——国库存银,八百万两。 这个数,说出去都没人信。堂堂大清,几亿人口,边塞要驻防,河道要修缮,文武百官要发俸,遇到灾年还得赈济。八百万两,够干什么?雍正记得清楚,康熙晚年的时候,国库虽然也不宽裕,但绝不止这个数。 他放下账本,对旁边的大太监苏培盛说:“更衣,去户部银库。” 苏培盛一愣,小声提醒:“万岁爷,外面天寒地冻的,要不传户部的人来问话?” 雍正没言语,只是瞥了他一眼。苏培盛赶紧低下头,不敢再多嘴。 皇帝的车驾出了紫禁城,直奔户部衙门。 路上行人稀少,寒风卷着碎雪,打在轿帘上沙沙响。 雍正闭着眼,手指轻轻敲着膝盖。他这皇帝当得不容易。先帝在位六十一年,晚年精力不济,吏治松弛,贪墨成风。 雍正接手的是个表面光鲜、内里千疮百孔的烂摊子。 户部的大小官员早就跪在门口迎接,一个个脸色发白,不知新皇帝突然驾临所为何事。雍正没下轿,只说了句:“去银库。” 银库在户部后院,重兵把守。厚重的库门上贴着封条,上面写着封印日期。雍正站在库门前,看着那封条,对库官说:“打开。” 封条被小心揭开,大锁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库门缓缓推开,一股陈年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。雍正迈步进去,苏培盛赶紧举灯跟上。 偌大的银库里,灯光昏暗。雍正眯着眼,慢慢扫视。库房里倒是整齐,一排排架子上码放着银箱。 可问题就在于,架子空了一大半。仅存的那点银箱,稀稀拉拉地摆着,像个掉了牙的老太太。 他走到一个银箱前,用手抹去上面的灰。箱子是满的,可这样的箱子,整个库房里找不出多少。他又走到库房深处,那里堆着些粮食和布匹,是实物税赋,数量也有限。 雍正没说话,只是默默地走了一圈,用手指敲了几个银箱,声音倒是实在。最后他停在库房中央,仰头看着高高的屋顶。梁上结着蜘蛛网,在灯光下晃晃悠悠。 跪在门口的户部官员们,汗都下来了。尚书徐元梦偷偷抬眼,想从皇帝脸上看出点端倪,可雍正面无表情。 “封上吧。”雍正终于开口,声音平静。 他转身走出银库,没再看那些大臣一眼。回宫的路上,他还是闭目养神,可手指敲膝盖的节奏快了些。 回到养心殿,雍正让所有人都出去,独自坐在炕上。八百万两。这个数字在他脑子里打转。先帝晚年对臣下宽厚,可宽厚过头了,就成了放纵。各省拖欠的税银有多少?大臣中饱私囊的有多少?皇亲国戚、八旗子弟,白白领俸禄的又有多少? 他想起当雍亲王时,就隐约知道国库空虚,可没想到空到这个地步。这哪是国库,这是个空壳子。 苏培盛小心翼翼地进来添茶,见皇帝盯着墙角出神,不敢打扰,正要退下,却被叫住。 “传怡亲王、隆科多、张廷玉。” 这三人是雍正的心腹。怡亲王允祥是他的十三弟,办事稳重;隆科多是步军统领,掌着京城的兵权;张廷玉是翰林出身,文笔好,心思细。 三人连夜进宫,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雍正没绕弯子,直接说了银库的情况。 “八百万两。”雍正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,“各位怎么看?” 允祥先开口:“皇兄,当务之急是开源节流。边疆不稳,用兵在所难免,这银子…” 隆科多性子急:“查!一查到底!臣就不信,这么多税银都飞了!” 张廷玉沉吟片刻:“皇上,此事不宜声张。一旦消息传出,恐生变乱。当徐徐图之。” 雍正听着,不置可否。他何尝不知道要查,可怎么查?从哪查起?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他刚登基,根基未稳,八爷党那些兄弟还在暗中窥伺。 “朕知道难。”雍正终于开口,“可再难也要办。大清朝不能毁在朕手里。” 他让张廷玉拟旨,以整顿吏治为名,要各省清查钱粮亏空。又让允祥暗中调查几个亏空严重的省份。隆科多则加强京城防卫,以防不测。 旨意发下去,朝野震动。谁都看得出来,新皇帝这是要动真格的了。有人拍手称快,有人惶惶不可终日。 雍正自己也知道,这条路不好走。会得罪多少人,会掀起多大风浪,他心里没底。可他更清楚,如果现在不动手,等局面无法收拾时,想动手也晚了。 那天晚上,雍正批阅奏折到很晚。烛光下,他的脸色阴晴不定。苏培盛来催了几次,他才放下朱笔,却毫无睡意。 他走到窗前,看着外面漆黑的夜空。紫禁城睡了,京城睡了,可这个大清帝国,却病得不轻。 他这个刚上任的“郎中”,能治好这个积重难返的病人吗? 雍正不知道。他只知道,从明天开始,这场硬仗必须打了。



![乾隆真是职业皇帝名不虚传[吃瓜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5141156089266685545.jpg?id=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