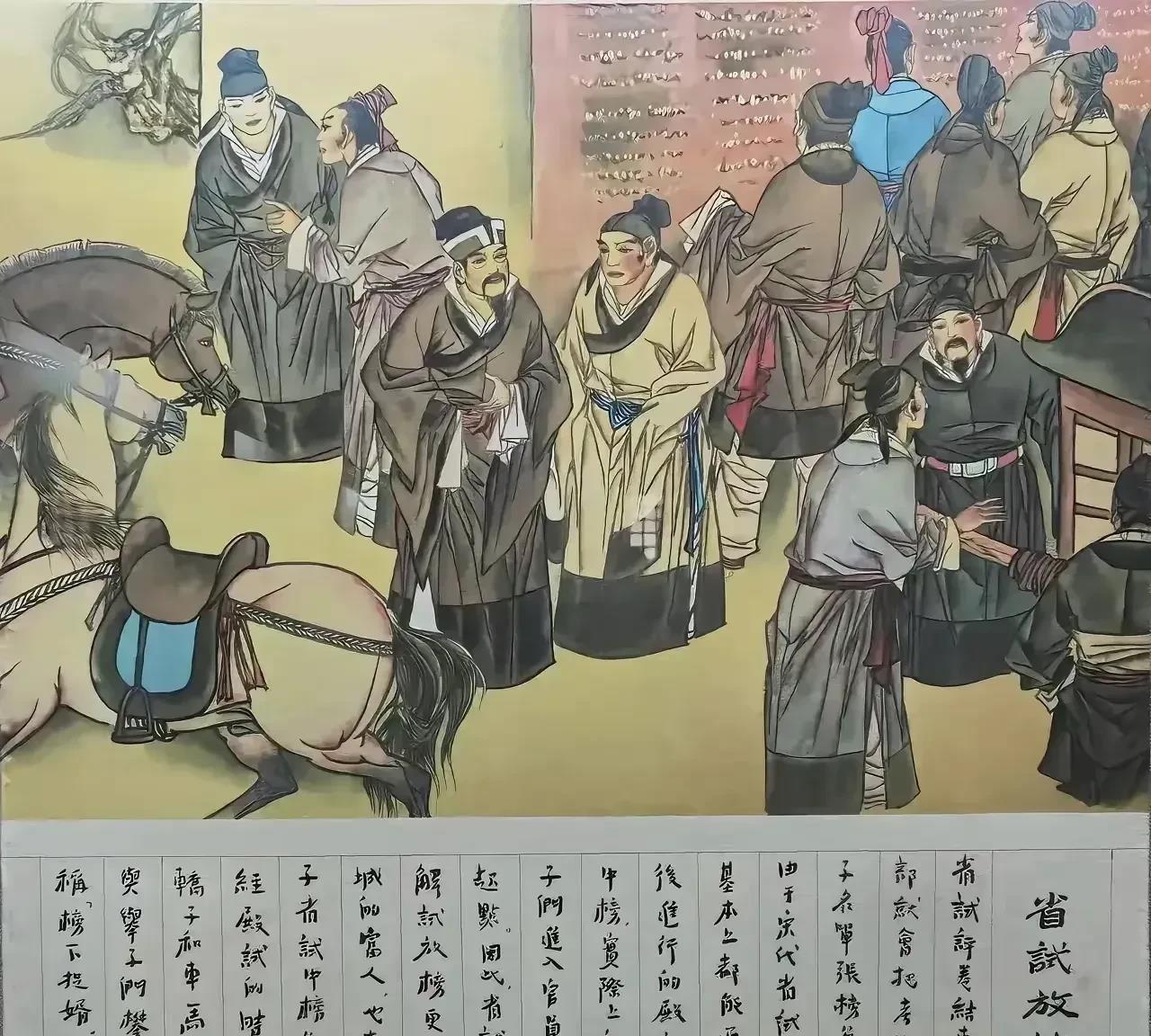公元 1034 年,年过半百的柳永第五次落榜。正蹲在汴京街头唉声叹气时,忽然被礼部差役叫住:“柳先生恭喜了!朝廷满五十送福利了。 柳永听见这话,手里攥着的半块干饼“啪嗒”掉在地上。他抬头时,看见差役手里晃着张黄纸,墨迹还带着新鲜的檀香味。这年他五十一岁,从弱冠考到白头,连考五次都折戟沉沙,连汴河岸边卖水的老汉都能背出他落榜后写的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。 差役把黄纸往他怀里一塞:“景祐元年新规矩,凡屡试不第、年过五十者,可凭此纸赴吏部注官。皇上说,不能让老书生空耗了一辈子。”柳永摸着纸上“特奏名”三个字,指腹蹭过边缘起的毛边,忽然想起二十八年前第一次进考场的模样——那时他穿着新浆洗的绿袍,腰里别着同科举子送的玉佩,以为笔下锦绣能轻易换个功名。 他终究还是去了吏部。穿惯了市井里的粗布长衫,换上从旧货摊淘来的官服时,袖口磨出的毛边硌得手腕生疼。授官的文书上写着“睦州团练推官”,一个从八品的小官,管的是刑狱诉讼。有人背后嚼舌根,说这官来得像朝廷发的救济粮,可柳永揣着文书走出皇城时,看汴河上的船帆都觉得比往常挺拔。 到了睦州,他倒没把自己当混日子的。见了知州吕蔚,不卑不亢递上名帖,不像别的新官要么谄媚要么怯懦。吕蔚原想这“奉旨当官”的词人不过是个摆设,没成想柳永审案子时,看卷宗的眼神比看姑娘的词稿还认真。有回县里报来个案子,说有个卖茶翁偷了地主的牛,柳永亲自去田间地头查访,发现是地主强占了茶翁的茶园,翁是气不过才牵走牛抵账。他把案子改判了,还把判词写得明明白白,连茶馆说书先生都能当段子讲。 可骨子里的东西改不了。公务之余,他还是爱往勾栏瓦舍钻。有回写了首《望海潮》,里头“东南形胜,三吴都会”几句传开,连杭州知州孙何都派人来请他喝酒。席间有人起哄,让他别再写那些“晓风残月”,多写点歌功颂德的应制词。柳永端着酒杯笑了,说笔在他手里,想写什么就写什么,就像当年落榜时,谁说“且去填词”他就真的填了一辈子。 后来他转任定海晓峰盐场监官,这地方偏僻得很,海风能把人吹得脱层皮。他看着盐民光着脚在卤水里踩盐,皮肤皱得像老树皮,就写了篇《煮海歌》,把“自从潴卤至飞霜,无非假贷充糇粮”的苦处全写了进去。有人说他不务正业,放着官不做好好当词人,他却把这篇歌行体刻在盐场的石碑上,说让后来的官都看看,这才是百姓的日子。 五十七岁那年,他终于得入京城,做了个屯田员外郎,还是个从六品。同僚里有当年同科及第的,如今早已是台阁重臣,见了他要么避着走,要么拿他的词打趣。他也不在意,照样在公文里写得一手漂亮字,闲了就去樊楼找相熟的歌妓,把新填的词谱上曲子。有次仁宗皇帝偶然听见唱他的“愿岁岁,天仗里常瞻凤辇”,笑着说:“这柳永,如今倒也懂些规矩了。” 其实他哪懂什么规矩,不过是看遍了沉浮。年轻时总想着“白衣卿相”的虚名,被皇帝一句“且去填词”堵得怨气冲天,觉得整个朝廷都欠他的。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才明白,这世间哪有那么多非此即彼。官服穿在身上,能为盐民说句公道话,比“金榜题名”四个字实在;词牌填在纸上,能让歌妓唱得有滋有味,比“御前献赋”更得人心。 皇祐五年的冬天,柳永死在润州的僧舍里。消息传到汴京,勾栏里的歌妓们凑钱给他办了葬礼,送葬那天,满城的丝竹都停了,只有她们哭着唱他写的《雨霖铃》。后来每年清明,都有歌妓去他坟前烧新填的词稿,这习俗竟延续了上百年。 有人说他这辈子活得拧巴,想当官偏要写俗词,写了俗词偏又放不下当官的念想。可柳永自己大概从不觉得拧巴。就像他词里写的“青春都一饷”,他不过是把这一饷的光阴,活成了自己的模样——没成状元,却成了“凡有井水处,皆能歌柳词”的柳三变;没入台阁,却让千年后的人记得,北宋有个词人,把官服穿得像长衫,把市井写成了江湖。 参考书籍:《宋史》《能改斋漫录》《乐章集校注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