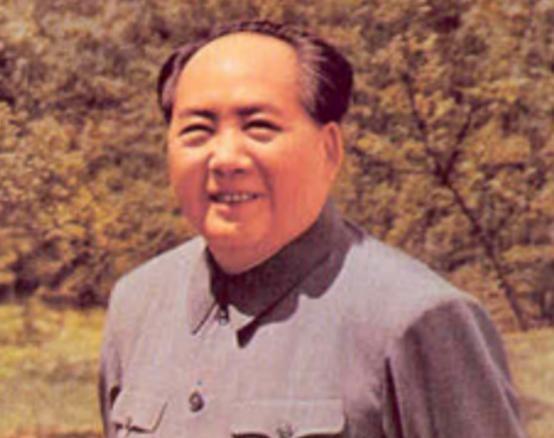1958年毛主席看《白蛇传》,情难自禁不停落泪,演出后不理睬法海 “1958年10月16日晚八点整,人都到齐了吗?”工作人员在上海干部俱乐部侧门低声催促。毛主席把帽檐压了压,淡淡一句:“先别急,青蛇还没上场呢。”一句戏言,把门口紧张的气氛冲得烟消云散。 那年秋天,主席第三次到上海视察。白天谈钢铁、看码头,夜里却只提出一个要求——“找个小剧场,给我来一出《白蛇传》。”同行的市委领导愣住了:钢材订数可以商量,节目单却一句都不能让步,这就是毛主席典型的“固执”。 他对这部戏是真痴迷。自1953年起,京、越、粤、昆四种版本的《白蛇传》唱片和胶片,他统统收藏;北京豪华音响没运到时,就在延安窑洞里用手摇留声机听。李银桥后来回忆:“主席翻箱倒柜找唱段,比找作战地图还上心。” 演出地点选在干部俱乐部的小礼堂,只能容纳三百来人。灯光一暗,他掐灭半截香烟,整个人像被吸进舞台。许仙初遇白娘子,他微笑;青蛇调皮,他轻轻点头;法海甫一亮相,脸色立即阴下去,双眉紧皱。 剧情推进到断桥诀别,台上胡琴一声哭腔,台下那位六尺男儿陡然红了眼眶。泪珠顺着腮帮滑落,他抬手抹净,又顺势为白娘子鼓掌,用力得掌心微微泛红。坐在旁边的市委书记偷偷递手帕,他摆摆手,像嫌破坏氛围。 雷峰塔镇压段最揪心。法海那句“妖孽,还不归位”,刚唱完,毛主席突然站起来,沉声一句:“欺人太甚!”声音不大,却压住全场。演员刹那间也跟着血脉偾张,嗓门更敞亮,连锣鼓点都拔高半调。 谢幕时,主席主动走上台。握青蛇的手,用双手;握许仙、白娘子,各一手;走到扮演法海的老生面前,只微微点头,便越过去了。台下有人偷笑,有人疑惑。演员愣了两秒,才明白这位观众的“入戏太深”。 事后闲谈,有人问他为何“怠慢”法海。他笑着反问:“你们读《水浒》时痛恨高俅不?我恨的也是角色,不是演员。”一句化解尴尬,却也透出一种率真:戏虽假,情是真,他就是要把喜怒哀乐搁在明处。 其实,这份认真贯穿他看戏的一生。早在1951年,他第一次看梅兰芳版《白蛇传》,散场就追着梅兰芳问:“为何额头只点一抹朱砂?”梅兰芳回家对夫人说:“世上挑扮相的人多,挑到那一点的人只他一个。” 主席不仅看,还挑,还改。1959年,他建议裘盛戎把《捉放宿店》里“望凌烟阁”改成“扬汉室美名”。理由简单:“历史不合。”裘盛戎连夜改词,后来逢人就说:“毛主席是我的‘总监制’。” 文化政策层面,他强调“古为今用,推陈出新”。1957年招待伏罗希洛夫,他力排众议定昆曲《林冲夜奔》。工作人员担心外国贵宾听不懂,他一句反问:“昆曲难懂,京剧就好懂?让他们看身段,听韵味。”那晚,伏罗希洛夫席间连竖大拇指,外交官们暗呼妙招。 地方戏他也扶持。湘剧演员左大玢初登主席台,紧张到忘词,他轻声提点:“慢点唱,别赶。”演完便劝她多读书,“嗓子是资本,脑子也是”。后来左大玢在田埂里演出摔倒,他听说后哈哈大笑:“稻茬拌脚,好戏更接地气。” 对粤剧红线女,他一句“多闻泥土气息”让她辞港返穗;对评剧新秀新凤霞,他提醒“别迷失在灯火里”;对京胡演奏家周宝才,他拿起琴弓试拉几下,笑道:“你拉胡琴,我来点评历史,再好不过。” 主席对戏曲的“情”又不止于行家把玩。看电影《雷锋》时,雷锋寄款给人民公社,他默默抹泪;听赴朝慰问团唱《长津湖》,他心口微颤。或许,那些人物让他想起太多牺牲的同志,想起连夜写下“卜算子·咏梅”时的寒风。 1975年,他腿脚已不利索,仍吩咐秘书调来湘剧录像。看至《陈三两》,他低声哼唱,忽然停住,说句:“韶山的山歌,也能编进去。”秘书记下,第二年湘剧团果真加了山歌引子,可惜等不到他亲耳听见。 许多演员回忆,毛主席的掌声带一点独特节奏,先轻后密,落点稳准。多年后,他们在各地舞台上再听到同样节拍,总会下意识回望后台——仿佛那位身着中山装的人正坐在灯影里,眼神温热,如当年雷峰塔下轰然一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