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,安庆市要拆掉陈独秀的老宅,改做自来水厂。曾经是新四军女战士的张君听闻此事后,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陈家门口,仿佛一尊门神守护着陈家老宅,不让拆迁人员上前半分。 1980年春天,安庆江风依旧,南水关一带却不再宁静。 市里扩建第二自来水厂的方案确定后,陈独秀故居赫然躺在施工蓝图中央。 那座在当地人嘴里叫作“陈家大洋房”的建筑,三天井四院,五开间六进,一百零六间屋宇像铺展开的棋盘,墙体混合中西风格,门楼高耸,花格铁栏透出俄式线条。 早年沿江船只过此,总会有人指着栅栏外的白墙感叹“这就是陈家的宅子”。 大宅不仅是陈家的居所,更是清末民初安庆财富与洋气交汇的象征。 房主人陈昔凡出身书香,又在东北任官,治水、安民、赈饥,政绩写进《怀宁县志》。 官声之外,他嗜古玩书画,北平琉璃厂开过“崇古斋”,沈阳另设分号,王石谷真迹挂满整面墙也不觉奢侈。正因这位父亲持守的财力与眼界,才有今日规模恢宏的陈家大洋房。 数十年后,大宅已成市土产公司仓库,木桁梁上还留着老匠人刻的花草纹样,只是灰尘遮住了光泽。蓝图公布那天,库管抬头望向屋脊,无意中瞥见天井上空一只麻雀掠过,随即在心里叹了一声:这片屋顶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 消息没传开多久,曾在新四军扛过枪的张君就听到了动静。 彼时她已是安庆图书馆馆长,正在修订《安庆史话》,手里攥着陈家宗谱和故居老照片。 张君认定,记录不如实物,故居在就有说服力,于是抄起一把竹椅来到南水关22号,在门槛外坐下,像一尊沉默的石像堵住拆迁队的车头。 路过的居民悄声议论,这位白发女同志脊梁挺得比门楼还直。 她不喊口号,只是每天翻开随身带的资料,静静等责任人出现。 市里负责基建的部门先派人来做工作,劝她理解城市发展。 张君翻出北京保留下来的几处四合院照片,对比手中的大洋房图纸,轻声一句“安庆也值得留一点”。 对方听完无话,只能记录诉求。 事态升级后,她写报告递市委、递省文物局,又坐火车到合肥找相关领导,拿出陈延年、陈乔年的革命事迹资料,说明这处宅院不仅关联陈独秀,还承载两位烈士的青春足迹。 省里两位分管副厅长到安庆调研,站在灰瓦屋檐下,感慨这里若保住,既是文化坐标,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现场。 可自来水厂选址已动工,一纸批文牵动供水民生,局面变得僵硬。 拆除的前夜,院内最后一次飘起饭菜香。 几名老库工收拾完货物,围在天井吃简单晚餐,偶尔抬头望破损玻璃窗,看灯影投射在二层回廊,像老照片里那些逝去的身影。 第二天清晨,推土机轰鸣穿透江面雾气,张君依旧守在门口,直到施工队领队亮出搬迁手续。 数小时后,高大的回字形楼体被切开口子,木梁折断声和瓦片碎裂声此起彼伏。 午后尘埃落定,曾经陈列古玩字画的厅堂化作砖石堆,南水关少了一段阴影,也少了一段可触摸的历史。张君在拆剩的一截青砖上坐了很久,袖口沾满灰,她没流泪,只说了一句“给后人留张照片吧”。 同行的摄影师按下快门,底片记录最后残影。 故居消失,但旋涡中激起的讨论持续发酵。 当地报纸连续刊文,学界开始检索城市扩张与旧址流失的案例。 几年后,国家层面陆续推出历史建筑测绘、控制性保护目录等制度,安庆也设立历史文化街区管控线。 张君退居二线时,把那把竹椅留在图书馆仓库,说“要为后来人留个坐下来的位置”。 年轻研究者整理她当年写的信函,上千页纸面承载一个普通人对城市记忆的执念。 今天行走南水关,很难再找到当年大宅的确切基址,自来水厂的管道在地下延伸,哗哗水声提醒人们它的重要性。可江风吹来时,仍有人指向大约的方向,小声说这里曾站过一座洋房,一位女馆长用整整七年时间诠释何谓守望。 历史没有给她一句胜利的回响,却因此留下一道更响的回声: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砖瓦,它镶嵌在为之奔走的人身上,也藏在后来人对这段往事的追问里。 未来的城市建设仍需供水管网,也需要一双双眼睛,去辨认街角老墙的纹路,去倾听院落深处的回声。时代前行时,倘若有更多目光愿意驻足,安庆的江风或许可以在钢筋水泥之间,继续讲述那些未竟的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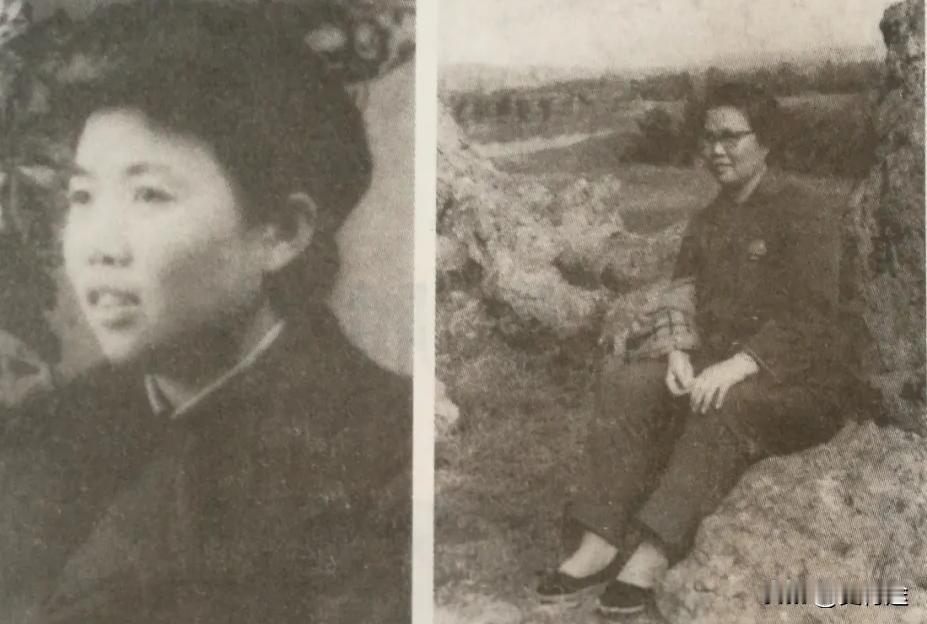



一路有你
向张君致敬!
吴忠民 回复 07-02 10:04
延年乔年都是了不起的人物[点赞][点赞][点赞]
海王子
安庆现在后悔了吗?
闲云野鹤
和北京城墙一样,只能一声“哎”!
用户10xxx32
应该在旧址为馆长立碑,致敬馆长,警示后人!
微斯人
想起了保护北京古城墙的林徽因先生
难得糊涂
一声叹息!
重庆-草帽王
安庆肯定后悔了
黑雪
政府想保留历史一定会保得住。
古道西风
人类社会和历史永远在发展之中,不可能面面俱到,所有名人故居都能得到保留。就建筑风格而言,各类只要有所保留就行,不必全部存世。在历史长河中,有多少遗址在地下不为人知?何必耿耿于怀于某时代一朵浪朵?
用户14xxx64
悲
用户10xxx48
唉!
用户10xxx66
如果安庆后悔,就应该调查决策过程公布出来,负责人有无违法!
用户10xxx02
陈独秀这地方,应该保存下来的
用户46xxx64
陈独秀,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,五四运动的领导者,其故居是应该要保留的。
希望
唉,可惜了
时代之声
1当年穷拆比修节省
用户13xxx42
江津有陈独秀故居,
用户60xxx05
可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