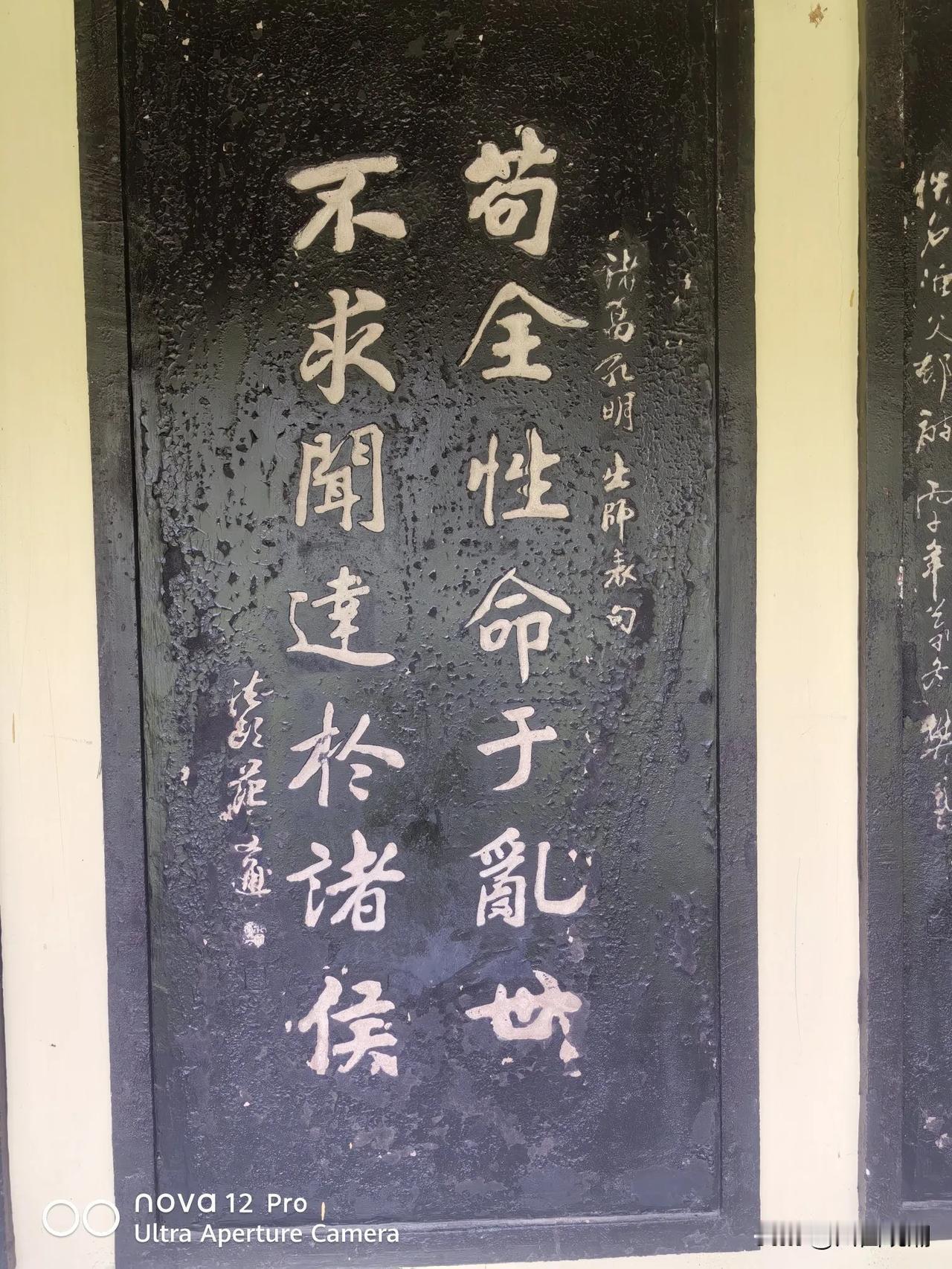理发店的镜子蒙着水汽,剃须刀在掌心震动时,总能听见老钟摆的滴答声。小张的推子在我发间游走,忽然停在耳后,像被往事绊住了齿轮:"今早又有个高三生跳了。"黄昏的光斜切过玻璃,把他围裙上的泡沫染成苍白色。 保险员的皮鞋踏过门槛时沾着春末的雨,他抖着伞说要去山上中学验尸拍照,语气里混着职业性的唏嘘。"蛇年才过一半,第三起了。"他掏出保单本,纸页间掉出片干枯的茶叶,"初八那个最可惜,初六刚开学呢。"我望着镜中自己微蹙的眉,突然想起老人口中正月里就亮起的教室灯,像提前抽芽的苦楝花,在料峭风里颤巍巍地开。 角落的藤椅吱呀响了一声,染黑的白发下漏出沧桑的笑纹。"现在的娃啊..."他卷起裤腿,膝盖上褐色的疤像褪皮的树皮,"我们那时候,五更天就着月光推磨,竹条子抽在光屁股上都是血印子。"他掰着粗糙的手指算兄弟姐妹,五个孩子在土窑洞里挤成暖烘烘的豆荚,清晨的冷风灌进破窗时,母亲的黄荆条总比鸡啼先到。 小张把热毛巾按在我后颈,忽然笑出泪来:"前几日帮收菜籽,那镰刀把儿磨得手起泡,可下工后攥着毛票买冰棍,一群人能从村头笑到村尾。"他说的农忙假早成了旧磁带,B面还留着割稻时蚂蚱跳上裤脚的痒。我想起自己洗啤酒瓶的夏天,指尖被玻璃划出道道红痕,却在收到水果糖时把疼痛含成了甜。 暮色漫进橱窗时,大爷的烟袋锅明灭不定:"三个女娃要去KTV挣钱,说比学裁缝轻快。"他吧嗒着烟,火星子溅在褪色的中山装上,像撒了把碎掉的星。小张用梳子敲了敲镜子,映出我们不同年代的皱纹:"当年缝件花衬衫能换两斤肉,现在年轻人嫌针脚太慢。" 我摸着口袋里的退稿信,想起从前趴在煤油灯下改稿的夜。4分钱100字的稿费,把月光都熬成了墨色,可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,比任何短视频都更让人踏实。如今理发店的电视总播着悬浮的成功学,却再难看见少年们挽起裤脚插秧的身影,他们的青春悬在教学楼顶,像朵等不到雨季的蒲公英。 离开时,门口的梧桐树正落新叶。小张在身后喊:"下周来给你修修鬓角。"我回头看他在暮色里擦着剪刀,金属反光里晃过无数张年轻的脸——有在田埂上追蝴蝶的,有在流水线前数糖纸的,还有在教学楼顶张开双臂的。时代的风掠过他们,有的长成了树,有的碎成了星,而理发店的镜子始终映着,那些被生活揉皱又展平的,关于青春与疼痛的剪影。散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