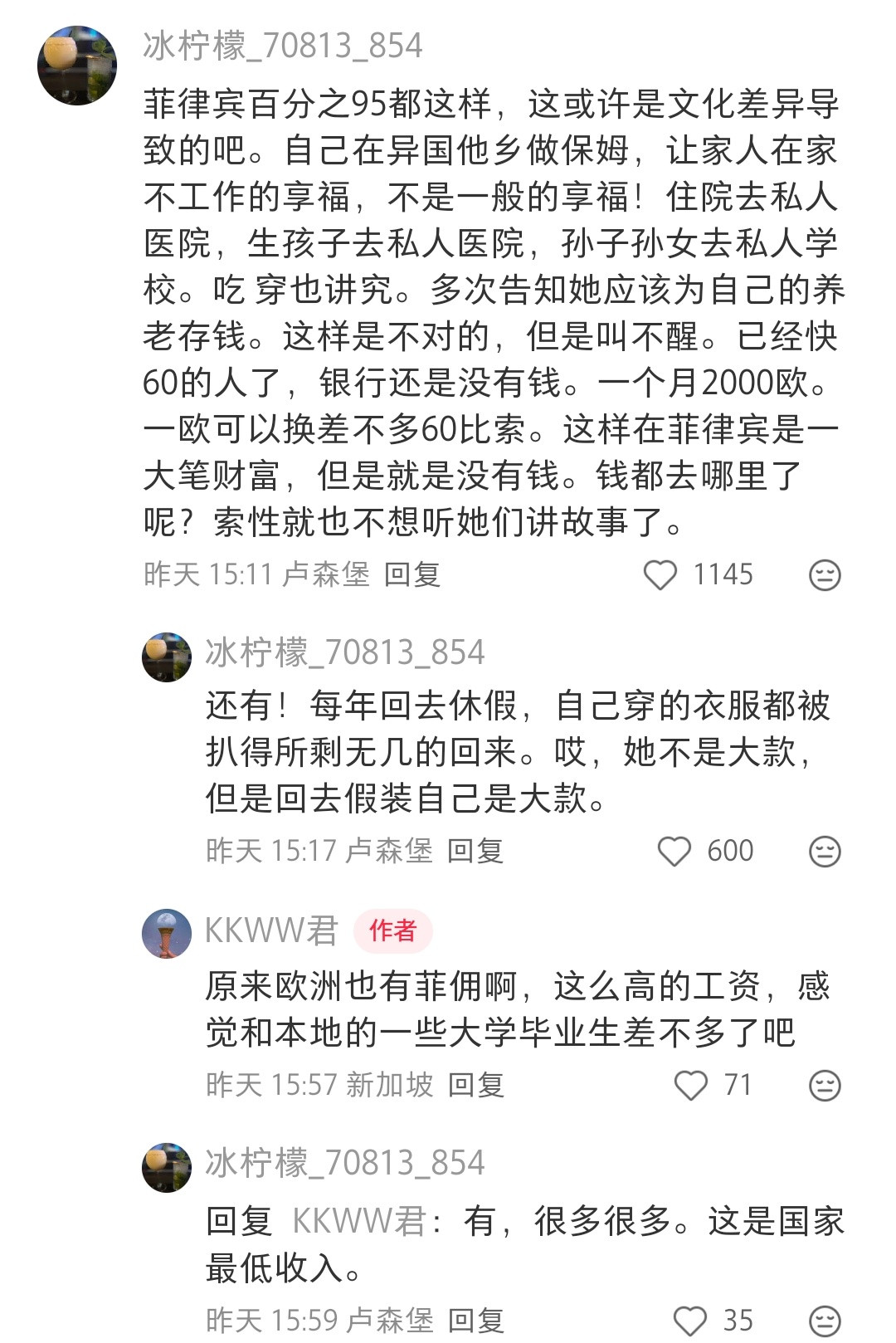1888年,山东一乞丐讨饭28年,终于攒下230亩田、3800吊钱,接着盖了一座大房子,谁料,他跑到穷人家里,挨家挨户跪下磕头:“求求你跟我走吧,我什么都包,还帮你干活。” 1888年,对于山东堂邑县柳林镇的人来说,是个极其炸裂的年份。 镇子东门外,一座崭新的大房子拔地而起。青砖灰瓦,名为“崇贤义塾”。这不是哪家地主为了光宗耀祖修的宅子,这是一个叫“武七”的叫花子,讨了整整30年饭,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学校。 学校盖好了,戏肉才刚开始。 按理说,出资人就是校董,那得高高在上。可武训干了件让所有人掉下巴的事。他跑到那些穷得揭不开锅的家里,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,噗通一声就跪下了。 这一跪,不是为了讨饭,是为了讨学生。 他对那些穷得叮当响的父母磕头:“让娃去念书吧,不收一分钱学费。娃家里的活儿要是没人干,我来帮你们干!” 为了让穷孩子读书,他把这一辈子的膝盖都跪烂了。 请来了举人崔隼当老师,人家是斯文人,武训觉得自己脏,不配同桌吃饭。开学宴上,他请老师和乡绅坐席,自己端个破碗蹲在门槛外面,等着吃人家剩下的残羹冷炙。吃着剩饭,他还乐呵呵地说:“先生吃好了,娃就能念好。” 你说这是卑微吗?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度的狂傲。他用这种把自尊心碾碎的方式,逼着所有的读书人、有钱人不得不正视这件事情:教育,比天大,比脸面大。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管理方式。现在的校长管老师靠考勤,武训靠“跪”。 老师如果偷懒,大白天睡觉,他不骂也不罚,他就静静地跪在老师床前,一声不吭。老师一睁眼,看到满脸污垢的出资人跪在床头,那得多大的心理阴影?羞愧得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,从此以后再不敢怠慢教学。 学生如果不听话,逃课去玩,他也跪。他跪在学生面前哭:“读书不用功,无脸见父兄。” 武训这种“变态”的执念,其实是被生活毒打出来的。 他本名叫武七,因为排行老七。7岁死了爹,跟着娘讨饭。那时候他也就是个普通的穷小子,直到14岁那年,他去给一个叫李老辫的举人家当佣工。 干了三年活,工钱一分没拿到。李老辫欺负他不识字,拿出一本假账,硬说工钱早都支完了,反咬一口说他讹诈。最后,武训被吊起来毒打一顿,扔出了大门。 在那个没人权的时代,文盲就是待宰的羔羊。 他在破庙里昏睡了三天三夜。醒来之后,那个原本老实巴交的武七死了,站起来的是一个发誓要向命运复仇的武训。 他复仇的方式很特别。他不杀人,不放火,他要办义学。他认准了一个死理:穷人之所以受欺负,就是因为不识字。只要让穷孩子都读上书,这世道就不敢再随便欺负人。 为了攒钱,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牲口。 20岁开始,他给自己剃了个阴阳头,留着怪模怪样的小辫子,见人就装疯卖傻。为了讨得几个铜板,他能当众吃蛇、吞砖头,甚至趴在地上学驴叫,让人当马骑。 周围人都笑他是个疯子,是个傻子。小孩子拿土坷垃砸他,他也嘿嘿傻笑。 他编了顺口溜唱:“我出力,你出钱,修个义学为贫寒。” 这哪里是乞讨,这分明是在炼狱。他把作为一个人的所有体面都抛弃了,把尊严揉碎了,换成那一枚枚带着腥味的铜板。 但是,这个“疯子”心里比谁都清醒。 他讨来的钱,哪怕是一个铜板,他都不花。烂菜叶子、发霉的馒头,就是他的口粮。攒够了一串钱,他立刻托信任的乡绅拿去放贷、买田。 这操作手段,放到现在绝对是顶级的基金经理。他一边行乞,一边搞土地兼并。只不过,别的地主兼并土地是为了享乐,他是为了让土地生出更多的钱,去盖学校。 这一攒,就是30年。 武训的努力没有白费。 继1888年第一所“崇贤义塾”后,他又在馆陶县、临清县接连办起了第二所、第三所义学。 这事儿终于惊动了朝廷。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曜听说了,不仅下令免了义学田地的钱粮税赋,还捐了银子。光绪皇帝更是颁给他“乐善好施”的匾额,赐名“武训”,甚至赏穿黄马褂。 一个要饭的,穿上了黄马褂,这是大清朝破天荒的头一遭。这黄马褂穿在身上,那是对整个官僚体制最大的讽刺——朝廷该干的义务教育,让一个乞丐给干了。 武训出名了,但他还是那个武训。 黄马褂他没穿过几次,依然穿着那身破棉袄,到处磕头求人读书。有人劝他娶个媳妇,留个后。他指着义学里的孩子说:“这些都是我的后。” 1896年,59岁的武训病倒在临清御史巷义塾的房檐下。临死前,他听到了教室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,脸上露出了笑容,就这样安静地走了。 出殡那天,三个县的百姓自发来送葬,哭声震天,人数达到了上万人。 直到1985年,武训才被正式平反。但教科书里提到他时,依然是寥寥数语,仿佛多说一句都会烫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