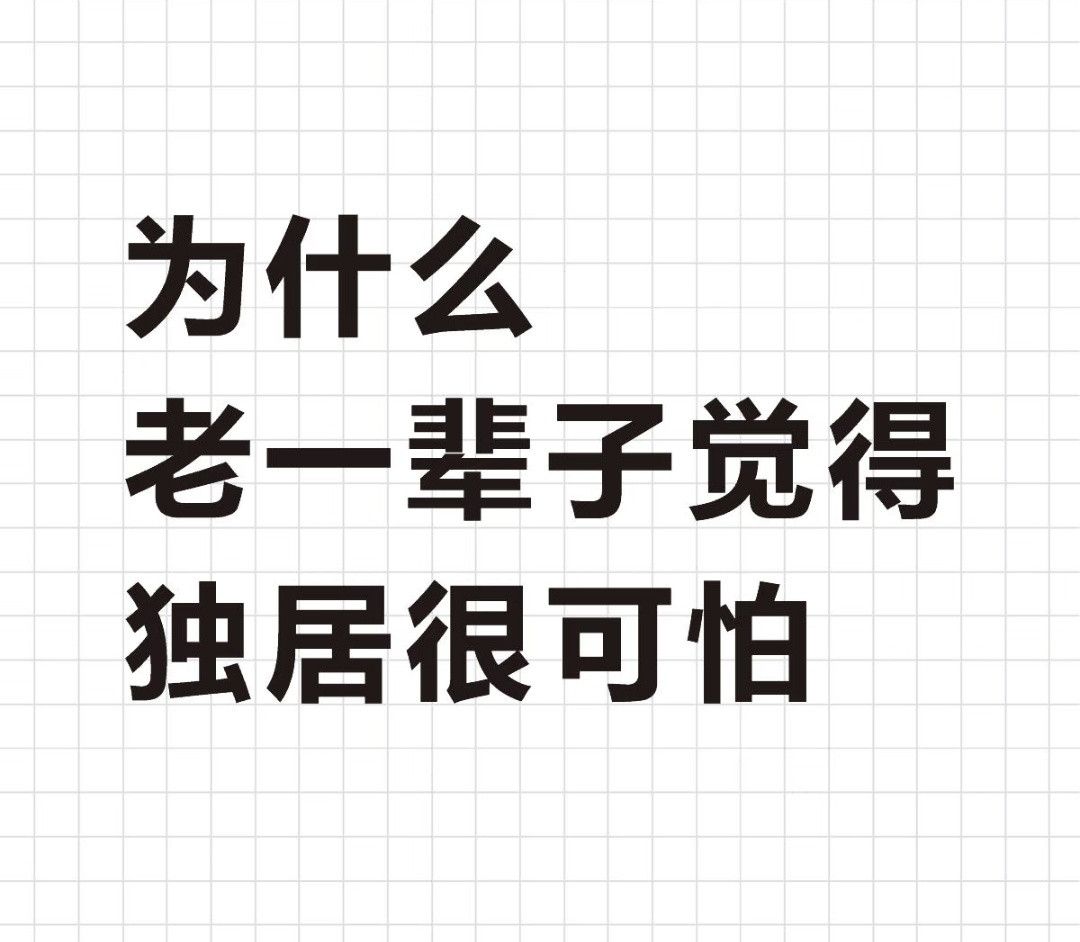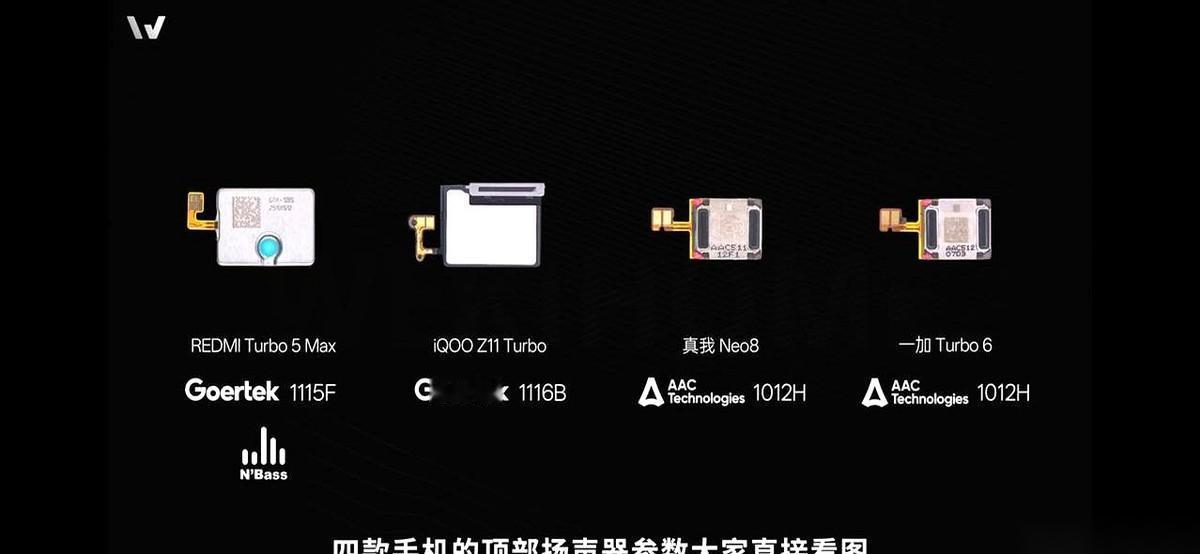有一种人,过年不回家。手机屏幕上,几百块一张的票,是他这个月剩下的全部饭钱。点下支付,下个月就要靠喝西北风续命。 出租屋里,一碗泡面的热气是唯一的温暖。窗外别人家的灯火,比天上的星星还亮,一阵阵的鞭炮声,听着像是在嘲笑。他划拉着手机,给家里群发了一条“过年好,加班忙回不去”,然后把手机往床头一扔,再也不敢看。 电话还是响了。老妈的声音从听筒里钻出来,先是问冷不冷,再是问钱够不够花。铺垫做足了,话锋猛地一转,“那个谁家的孩子,跟你一样大,二胎都满地跑了……”他拿着电话,走到窗边,看着楼下小孩举着烟花跑过去,嘴里“嗯嗯啊啊”地应付着。 电话一挂,屋里瞬间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隔壁传来一家人看春晚的笑声,穿透了薄薄的墙壁,每一下都敲在心上。 还有一种人,是真的没地方回了。通讯录从头翻到尾,那个永远置顶的号码已经变灰。想打个电话,说一句“我挺好的”,听筒那边却只有一片虚空。所谓的“家”,成了一个户口本上的地址,一个记忆里的坐标。 夜深了,他就一个人,对着一盘速冻饺子,打开了电视。万家灯火,好像没有一盏是为他亮的。 说白了,哪有什么不想家。所谓的“年味儿”,对有些人来说,早就成了一场需要凭票入场的仪式,那张票的名字,叫“混得体面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