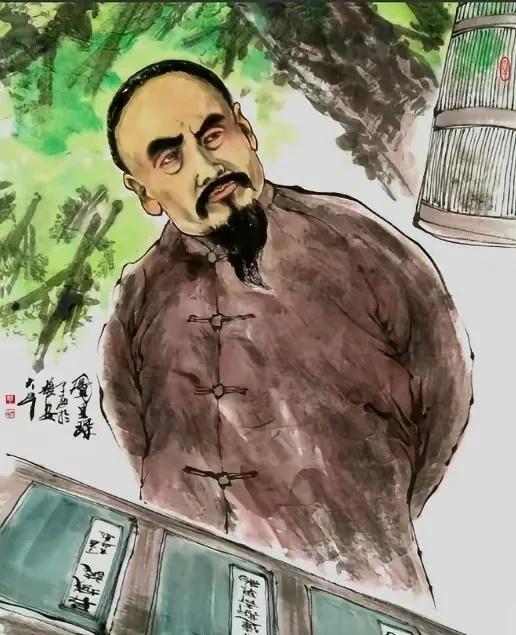1860年深秋,安庆城下,曾国藩把湘军的老本全押了上去。咸丰皇帝催他去救苏州、常州的诏书一封接一封,他压着不办;英法联军打进北京,朝廷调兵勤王,他照样一个兵都不给。这人不傻,他知道安庆是天京的命根子——丢了安庆,太平天国就像被掐住喉咙的死囚。可他玩的不是硬碰硬,是“围点打援”:城里守军饿到吃树皮、嚼老鼠,甚至人吃人,他就是不急着破城;谁来救,他就打谁,一刀一刀放干太平军的血。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“关注”,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,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,感谢您的支持! 陈玉成是真急了。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,十四岁就从军,武昌登城、镇江闯围、三河全歼湘军精锐,他这辈子没打过这么憋屈的仗。他带着人马从庐州扑向安庆,一次、两次、三次,像撞南墙一样往曾国荃挖的那两道壕沟上撞。湘军的壕沟挖得又深又宽,前面是围城的内壕,后面是拒援的外壕,两万太平军填进去,连个响都没听见。 安庆城里的哭声传不出来,但陈玉成听得见。那是一万六千多条人命在油锅里煎的声音。 可真正要了他命的,不是曾国藩的壕沟,是自家人的算盘。 洪仁玕那套“围魏救赵”的计策,纸上写得漂亮:陈玉成从北岸打武汉,李秀成从南岸打武汉,两路夹击,逼湘军回救。问题是,李秀成压根没打算配合。他从江西转了一圈,收了二十几万人马,却对进攻武汉磨磨蹭蹭。陈玉成二月初八攻下黄州,武汉城里只剩两千守军,唾手可得——可他等了四天。这四天里,他在等李秀成,等来的却是英国人的几句空话和捻军在松子关兵败主帅阵亡的消息。 后人总爱说陈玉成被巴夏礼骗了,洋人吓唬他不敢打武汉。这话听着顺耳,把责任推给外人多省事。可真相是:打下黄州的第二天,陈玉成就把兵力调往罗田方向了。他在救捻军,救那位一直支持太平天国的龚得树。结果人没救成,五万捻军溃散,龚得树阵亡,他围攻武汉的最佳时机就这么耗光了。 这不是洋人害的,是自己优柔寡断。 等他再回头救安庆,曾国藩已经把绞索收紧了。更讽刺的是,安庆北门外那个让他吃尽苦头的太平军守将程学启,最后被曾国荃用养母威胁,带着三百人投了湘军。这个叛徒亲手给湘军指路挖地道,炸药一响,安庆北城墙塌了。你说这是命?这是人心散了。 陈玉成退守庐州,外面是湘军铁桶般的包围,里面是天王洪秀全的斥责诏书——“屡救安庆不力”。他守了几个月,油盐都断了,外援全无,最后决定突围。往哪儿走?寿州。那里有苗沛霖。 苗沛霖是什么人?凤台一个读书人,考不上功名,靠办团练起家。这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:看风向。他投太平军,收过陈玉成的封号;他降清廷,又跟胜保称兄道弟。他自称“先生”,让手下喊他“先生”,不穿清朝官服,也不剃发——留着辫子但不全剃,剃了也不戴顶戴。这是个乱世里长出来的毒蘑菇,谁给好处就靠谁,谁要倒台就踩谁。 陈玉成不是不知道苗沛霖反复无常。可他没有选择了。庐州待不住,往哪儿跑?他带了二千人,走到寿州城下。苗沛霖称病不出,派侄子苗景开迎接。进城那天,中津渡口的浮桥刚过完就被拆了。陈玉成刚进厅堂,伏兵四起,他被摁在地上五花大绑,抬头大骂:“苗贼!老子瞎了眼!” 苗沛霖躲在后堂,一声不吭。 胜保劝降,陈玉成说:“大丈夫死就死,啰嗦什么?”他被押往北京,走到河南延津,圣旨到了:凌迟处死。那一年他二十六岁。从金田起义算起,他打了整整十二年仗。 曾国藩说他“自汉唐以来,未有如此悍贼”。这话从一个死敌嘴里说出来,分量比任何褒奖都重。 可我想说,陈玉成这辈子最可惜的,不是死在战场上,是死在“自己人”手里。李秀成没来,洪仁玕指挥不动,洪秀全猜忌,苗沛霖出卖——他不是打不过湘军,是身后全是坑。一个靠战功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的年轻人,到头来发现自己其实是个孤军。 太平天国那些王爷们,哪个不是在盘算自己的地盘、自己的人马?陈玉成的地盘在皖北,那是他从湘军手里一寸一寸夺回来的;李秀成的地盘在苏南,打得富庶也守得安逸。洪仁玕说要两路救安庆,李秀成嘴上答应,脚底下压根没往武汉迈。后来安庆失守,天京倒计时,李秀成也急了,可他再急也晚了。 英雄末路最可悲的不是被敌人打败,是被自己人当成弃子。 苗沛霖后来也没得好死。湘军腾出手来收拾淮北,他困守蒙城,趁夜逃跑,被手下砍了脑袋,献给僧格林沁。胜保保不住他,他那一套看风使舵的把戏,到头来连自己都栽进去。可这有什么用呢?陈玉成回不来了。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,历史从来不缺英雄,缺的是让英雄不被辜负的土壤。陈玉成的悲剧,一半是曾国藩的深沟高垒打出来的,一半是自己人那颗分崩离析的心喂出来的。安庆保卫战与其说是湘军打赢的,不如说是太平天国内部先认输了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