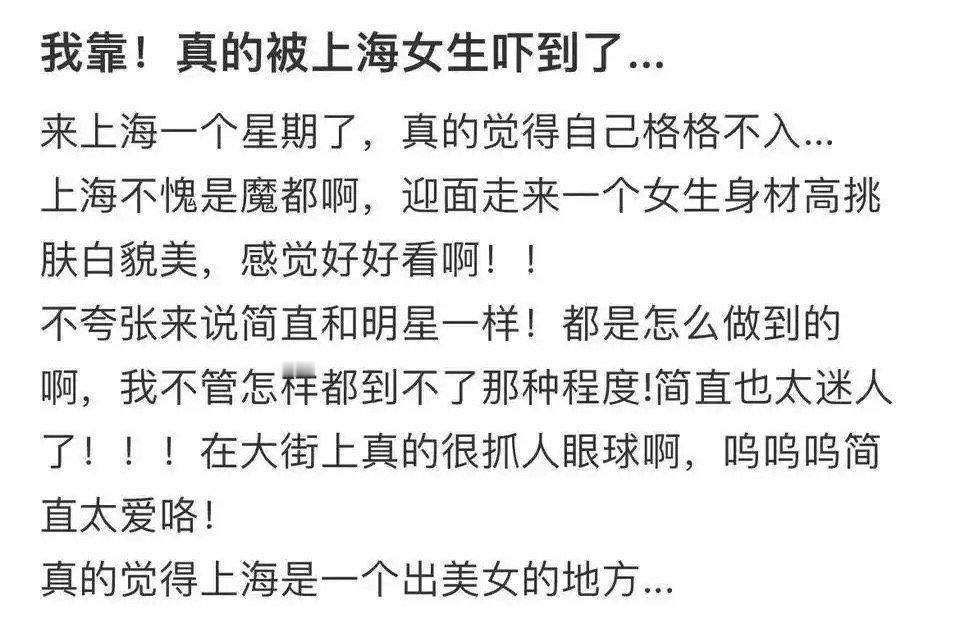太寒心了!上海一位老人去世后,远在国外的女儿火速赶回,刚出浦东机场就打了三个电话。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居委会的李主任。李主任接了电话,声音里带着点疲惫,说老人是三天前早上被发现的,社区网格员按例上门探访,敲了半天门没反应,联系开锁师傅打开门才发现人已经没了,身上没明显外伤,法医来看过说是自然死亡。 她捏着手机站在机场出口,秋风卷着细雨打在脸上,凉得像父亲最后一次视频时的声音——那时候她只当是信号不好,没听出话里的颤抖。 出租车驶过黄浦江时,她终于忍不住拨了第三个号码——堂弟苏明的电话。 电话响了七声才被接起,背景音里有麻将牌碰撞的脆响,像在敲她的心。 “姐,你到上海了?”苏明的声音含混,带着刚睡醒的惺忪。 “我爸走了。”她盯着车窗上的雨痕,声音平得像结了冰的湖面。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,传来“哗啦啦”的洗牌声,“我……我前几天加班,没顾上看消息。” “加班?”她想起张阿姨在第二个电话里说的,“你爸摔断腿那天,我看苏明陪着个姑娘在小区门口买奶茶,喊他他装没听见”,心口猛地一缩。 出租车停在老小区门口,她拖着行李箱往里走,石板路上的青苔沾湿了鞋跟。 三楼的防盗门还是她出国前换的密码锁,按“晴晴生日”那串数字时,指尖突然抖得按不准键。 门“咔嗒”一声开了,一股混合着灰尘与桂花味的冷气扑面而来——客厅窗台上的桂花盆栽枯了大半,花瓣落得茶几上到处都是。 沙发扶手上搭着件灰蓝色毛衣,针脚歪歪扭扭,领口处还别着枚银色顶针,那是她出国前给父亲买的,他总说戴着织毛衣“顺手”。 她伸手摸了摸,毛线还带着点潮意,像父亲没说完的话。 这时才想起第二个电话里,张阿姨哽咽着说“你爸上个月摔了腿,躺床上还念叨要给你织件厚的,说国外冬天冷”。 茶几上摆着副象棋,红方的“马”悬在“楚河汉界”上,旁边压着张泛黄的纸条:“晴晴小时候教我的‘马走日’,今天又忘了怎么走,等她回来问她。” 厨房飘来股馊味,她走进去,看到灶台上放着个白瓷碗,半碗粥凝在碗底,上面浮着层绿霉,旁边还放着个没洗的勺子。 她蹲下来,手指碰到碗沿,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爬到心里——这是父亲最后一顿没吃完的饭吗? 收拾衣柜时,一个硬壳笔记本从毛衣堆里滑出来。 封面是她小时候画的全家福,褪色的红蜡笔写着“爸爸的晴晴”。 翻开第一页,钢笔字歪歪斜斜:“晴晴今天视频说升职了,我得装作没看见她眼下的青黑,她总说自己不累。” 再翻一页:“腿摔了,医生说骨裂,不敢告诉晴晴,她项目正到关键时候。张阿姨送了碗排骨汤,我说‘谢谢’,其实想让她多坐会儿,又怕耽误她接孙子。” 那些她以为的“一切都好”,究竟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疼? 李主任后来又打来电话,轻声说“你爸前段时间总来居委会问,说想办个老年食堂志愿者证,‘小区里好几个老伙计跟我一样,孩子不在身边’”。 她当时没接话,现在才明白,父亲说的“老伙计”,其实是在说他自己。 葬礼那天苏明来了,捧着束蔫了的白菊,站在人群后不敢上前。 她看着他,突然想起父亲日记里写“苏明送了箱牛奶,说忙完这阵带女朋友来吃饭”——原来那句“忙”,是忙着忘记这个独居的伯父。 她没理他,只是蹲下来,把那副象棋摆在父亲墓前,替他把悬着的“马”跳到了“卒”的旁边——这是她小时候最爱用的招数,父亲总故意让她赢。 回国后的第三个月,她在社区公告栏贴了张通知:“夕阳红关爱基金成立,为独居老人提供送餐、陪伴服务。” 落款处,她画了朵小小的桂花。 那天回家,她学着父亲日记里写的步骤煮了锅桂花粥,盛出来放在茶几上,对着空荡荡的沙发说:“爸,粥熬好了,这次没馊。” 秋风从窗户缝钻进来,吹动了沙发上那件织完的毛衣,衣角轻轻扫过她的手背,像父亲从前的抚摸。
几百万存款却成了废纸最近这两天,有一个视频,不知大家看了没有。说上海一位单
【480评论】【336点赞】

![没钱上海只是上海,有钱哪里都是上海[吃瓜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2375813697858735623.jpg?id=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