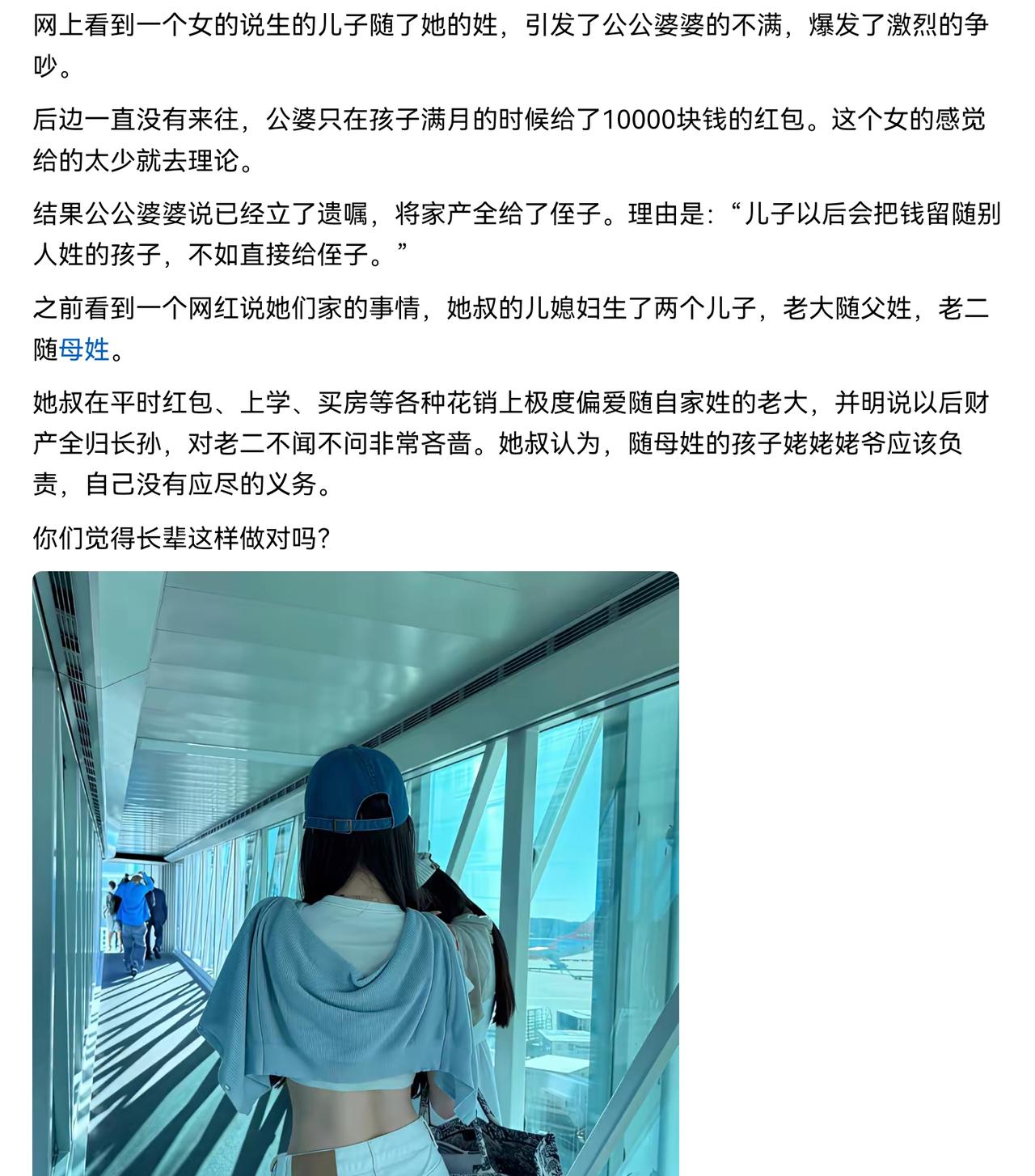我三姨做鸡大半辈子,现在老了病重手术姑娘都不给她签名。亲戚外甥女没一个主动联系她,找个老头还跟她砸窗掀桌的。三姨年轻时候长得是真好看,大眼睛高鼻梁,梳着两条大辫子,走在路上回头率老高了。那时候家里穷,她又是老大,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,我姥爷重男轻女,总说“丫头片子早晚是别人家的人”。 病房的白墙映着她枯瘦的手,手里攥着张泛黄的黑白照——照片上的姑娘梳着两条油亮的大辫子,辫梢垂到腰际,大眼睛在1970年代的阳光里闪着光,那是我三姨,那年她十七。 家里穷得叮当响,她是老大,下面三个弟妹等着吃饭,姥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,烟圈里总飘着一句“丫头片子早晚是别人家的人”。她没念完初中就辍了学,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,晚上偷偷纳鞋底换粮票,辫子梢总沾着麦秸灰。 十八岁那年她第一次离开家,背着蓝布包袱站在村口,辫子被风刮得乱晃,弟弟追出来塞给她半块红薯,说“姐,你早点回来”,她没回头,怕一回头就走不了。后来听说她在南方“讨生活”,寄回家的钱越来越多,盖了瓦房,供弟弟上了大学,只是信里的字越来越少,最后只剩汇款单。 女儿出生那年她三十岁,抱着孩子拍了张照片,照片里她剪了短发,说是“干活方便”,孩子眉眼像她,却没她当年的灵气。她试着给孩子梳辫子,孩子却哭着扯掉皮筋,说“同学笑我妈是……”后面的话她没听清,只觉得手心里的梳子硌得慌。 现在她躺在病床上,大夫拿着同意书问“家属呢”,她摸出手机,通讯录里“女儿”两个字按了又按,最终没拨出去。前几天女儿来医院,站在病房门口,说“我没爸没妈,你也别认我”,转身时,她看见女儿鬓角有颗和她一样的痣。 有人说她“不检点”,可那年头,一个没读过书的姑娘,要养活三个弟妹,除了没日没夜地干活,还能怎么办?她挣的钱,一半寄回家盖了瓦房,一半供弟弟上了大学,自己却在三十岁那年累垮了身子,辫子也剪了,说是“干活方便”。 姥爷的那句“丫头片子”像道符咒,她一辈子都在证明自己不是“别人家的人”,可当弟弟们成了家,有了体面工作,她却成了亲戚嘴里“丢人现眼”的存在——他们忘了,当年是谁踩着露水去赶集,用省下的口粮换弟弟的学费;忘了她冬天冻裂的手,缠着布条纳鞋底的样子。 她现在总对着窗户发呆,窗玻璃上有道裂缝,是上个月那个老头砸的,他吼着“你这种女人就不该有家”,可他不知道,她当初收留他,只是因为他说“我给你暖脚”,像极了当年弟弟塞红薯时的眼神。 你说,一个女人这辈子,到底要攒多少眼泪,才能把年轻时的光重新攒进眼睛里? 手术同意书在床头柜上放了三天,边角都卷了。 她的大辫子成了旧照片里的影子,再没人提起。 或许我们都该学学,在评判别人的人生之前,先问问自己:如果换成是我,在那个年代,背着一家人的希望,我能比她走得更体面吗? 昨天护士来换床单,从枕头下摸出个布包,里面是一小束头发,黑中带白,编得松松垮垮,像两条没力气的辫子。她笑了,说“当年要是不剪,现在该到脚踝了吧”,声音轻得像风,吹过病房,也吹过那些被遗忘的时光。
昨晚家庭聚餐,我直接掀了桌子!就因为我妹当着亲戚面数落我媳妇小气,我当场怼她:先
【2评论】【5点赞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