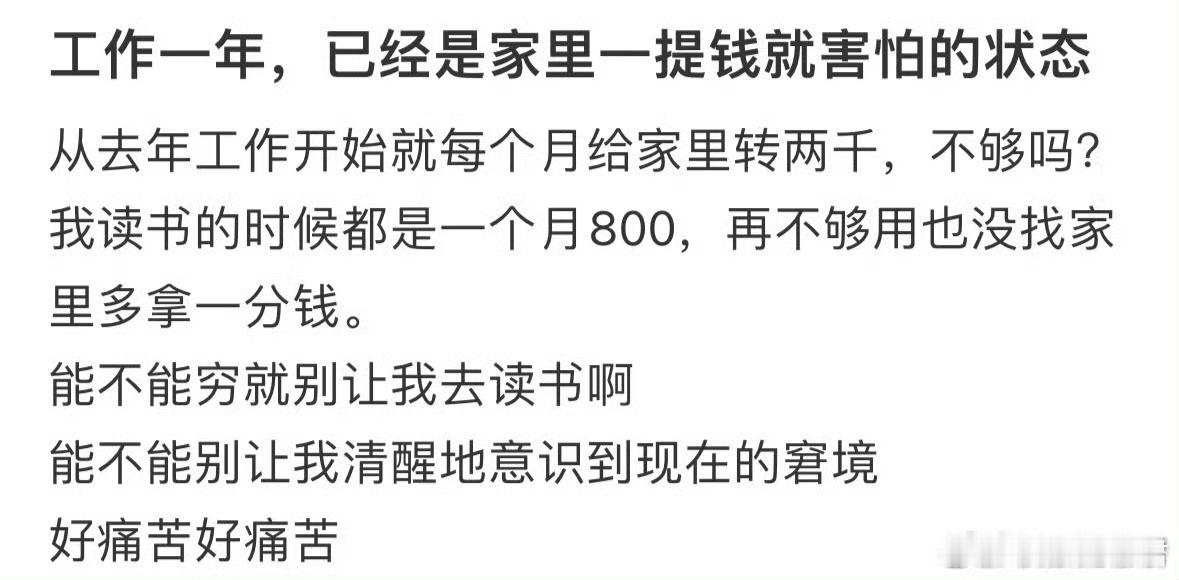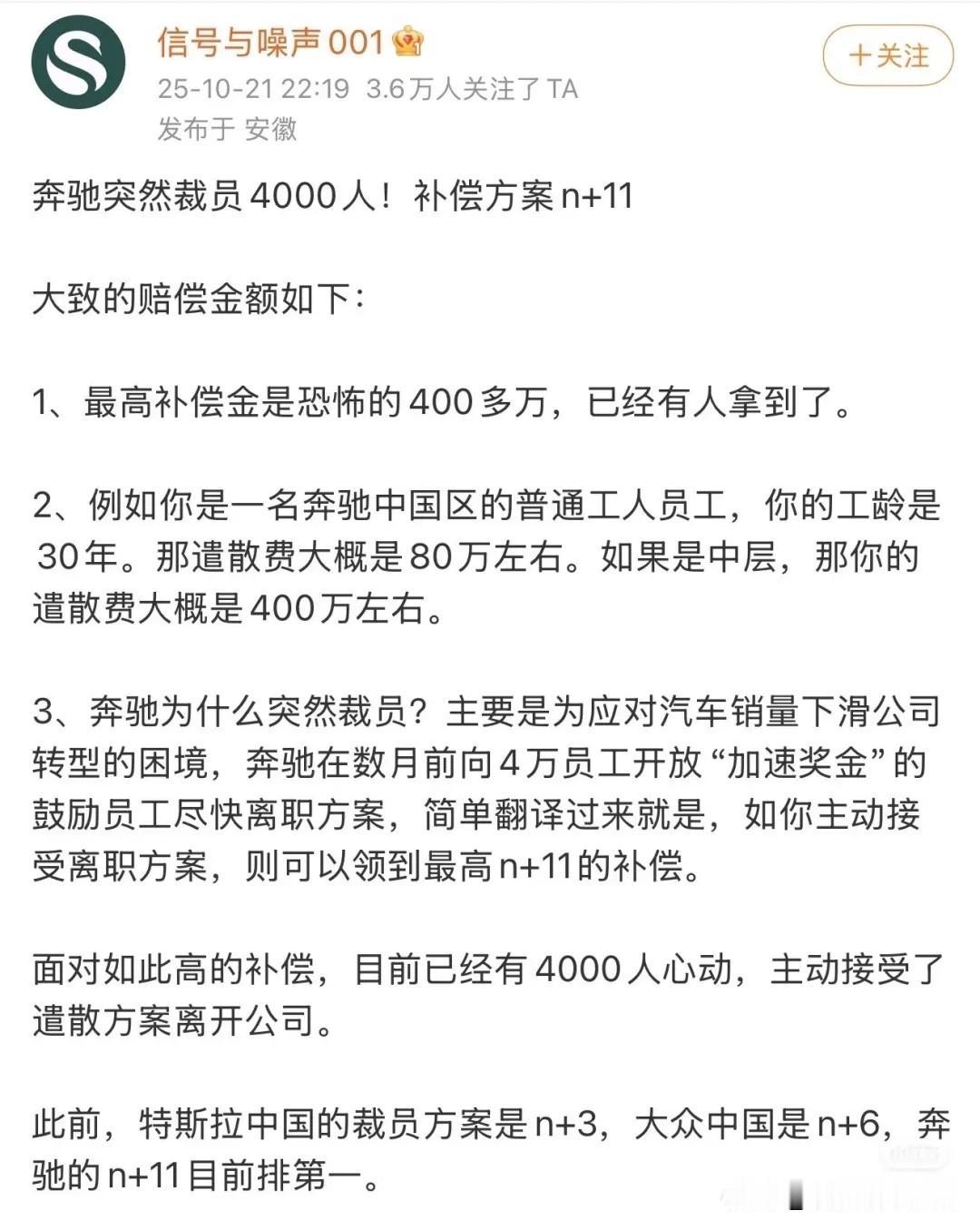他判刑13年至死未平反,10万人送行墓前立百碑,百姓说不能忘了他。 提起兰考,人们首先想到焦裕禄,但在当地那片深厚的黄土地里,还埋着另一段甚至更显沉重与传奇的记忆,如果你走进那片墓园,会被一种罕见的景象震撼:不是统一规划的豪华陵寝,而是杂乱地立着一百多块石碑。 这些碑,没有一块是官方立的,全出自甚至连名字都凑不齐的老百姓之手。碑下睡着的老人叫张钦礼,一个至死都没有保留党籍和公职的“犯人”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,那时候的干部,配车是身份和权力的铁证,更是一道将“官”与“民”隔开的屏障,1968年,张钦礼升任相关职位,组织给配了一辆吉普车。 在旁人眼里这是威风,在他眼里这是负担,他开着车下乡,隔着玻璃窗看窗外的黄沙漫天,看面黄肌瘦的乡亲,心里堵得慌,他有一套独特的算账逻辑:这铁皮壳子只要不动,就是在糟蹋钱,而老百姓正等着那口救命粮。 于是,这位可以说是最“败家”的干部,转身就找人把那辆让人艳羡的吉普车卖了八千块,这一大笔钱,连个响声都没听见,转身就全部分给了最穷的生产队买粮。 过了两年,坐骑升级成了价值三万的华沙轿车,他不仅重演了“卖车换粮”的戏码,甚至把自己压箱底攒了一辈子的一万五千元私房钱全搭了进去。 在他看来,那堆在院角渐渐生锈的破自行车,远比轿车好用,车轮子在土里滚,人才能听见地里的实话,那一辆辆被骑废的自行车,实际上是他作为考城县县长时期,用双脚丈量两百多个村庄画出的“活地图”。 他和焦裕禄,就像这片盐碱地上长出的两棵硬树,两人第一次碰面,张钦礼没讲虚头巴脑的客套,直接把焦裕禄拉到了风沙肆虐的东坝头。 在那场著名的张君墓镇风沙暴里,两人躲在土窑洞里避难,外头黄沙封门,焦裕禄发誓治不好沙对不起百姓,张钦礼就一句承诺:“您指哪儿,我就打哪儿。” 这不是场面话,是拿命在填。为了找治沙的泡桐树苗,他骑着那破车跨县去求人,脸面全然不顾;焦裕禄去世后,他顶着压力继续带着大伙挖河渠、改盐碱。七年时间,十九万亩防护林硬生生挡住了风沙,让兰考如今能产出销往全国的桐木乐器,这绿色的底色里,有一半的汗水姓张。 可1979年的那个冬天,风向变了,曾经的劳模成了阶下囚,十三年的刑期压在了他身上,在监狱的那四千多个日夜里,他静得像那口枯井。 他帮狱警理档案,帮犯人看病,唯一的执念还是兰考的树活没活,人饱没饱,女儿哭着去探监,他反倒安慰说不做亏心事,公道在人心。 等到1990年,当那个背已驼、发全白的老人走出高墙时,监狱门口站着的不是官员,而是手里提着自家蒸的馒头、地里刨的红薯的兰考老农,那一刻,几十个汉子默默流泪,一句话说不出来,只是围着他。 没有平反文件,没有退休工资,晚年的张钦礼全靠儿女接济,但他只要一回兰考,就又闲不住了。 哪家孩子上不起学,哪个学校操场烂了,那个没权没钱的糟老头子又开始四处张罗。他不避讳自己坐过牢,只说一句“群众心里有杆秤”。 在2004年5月他离世的那天,没有任何机关下发通知,也没有谁去组织动员,十万多名群众仿佛听到了某种无声的号令,从郑州一路绵延到兰考。 长达五个小时的路程里,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。那些拄着拐杖走不动的白发老人,那些跪在路边嚎啕痛哭的妇女,把这场葬礼变成了新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民意洪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