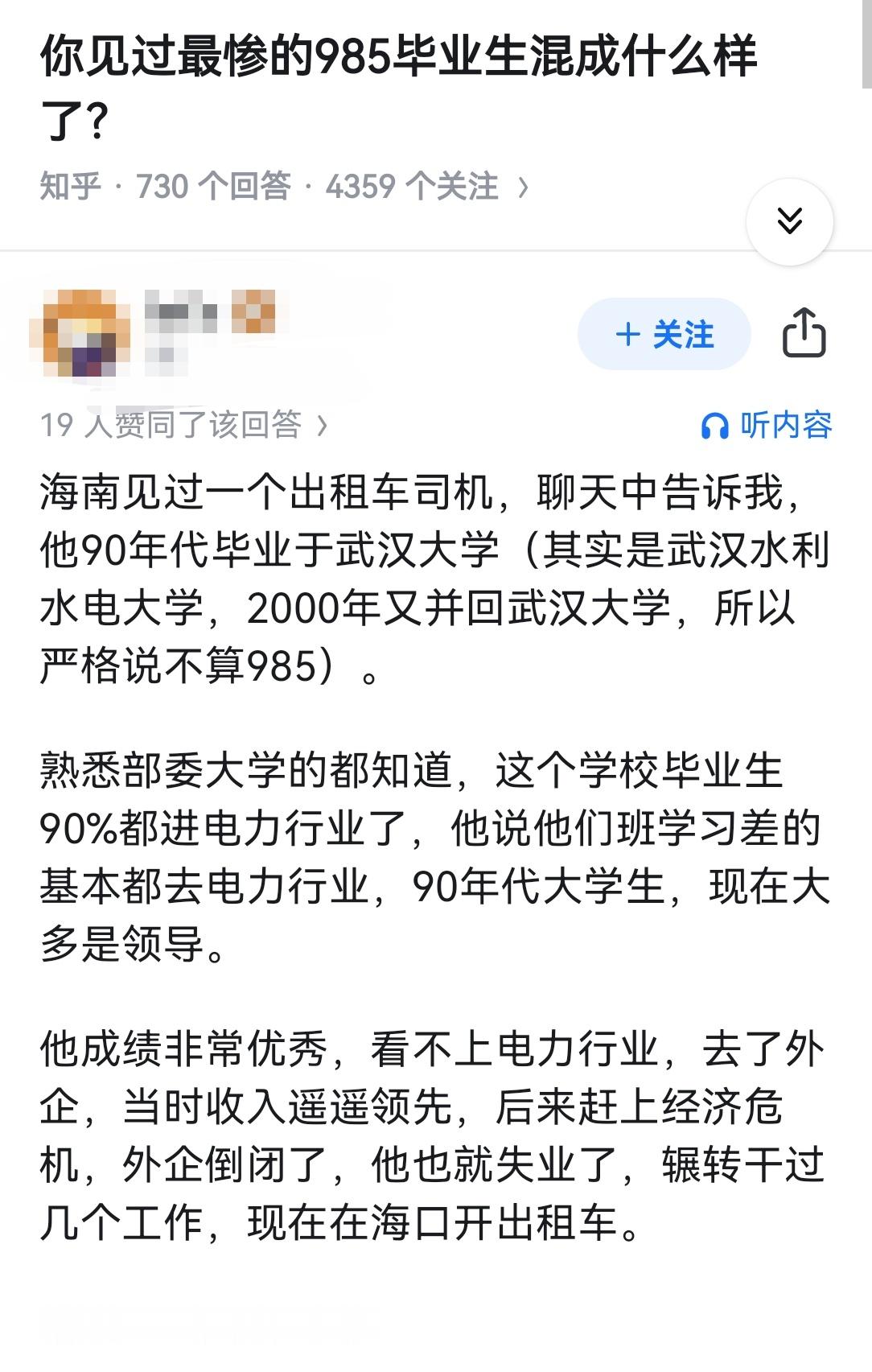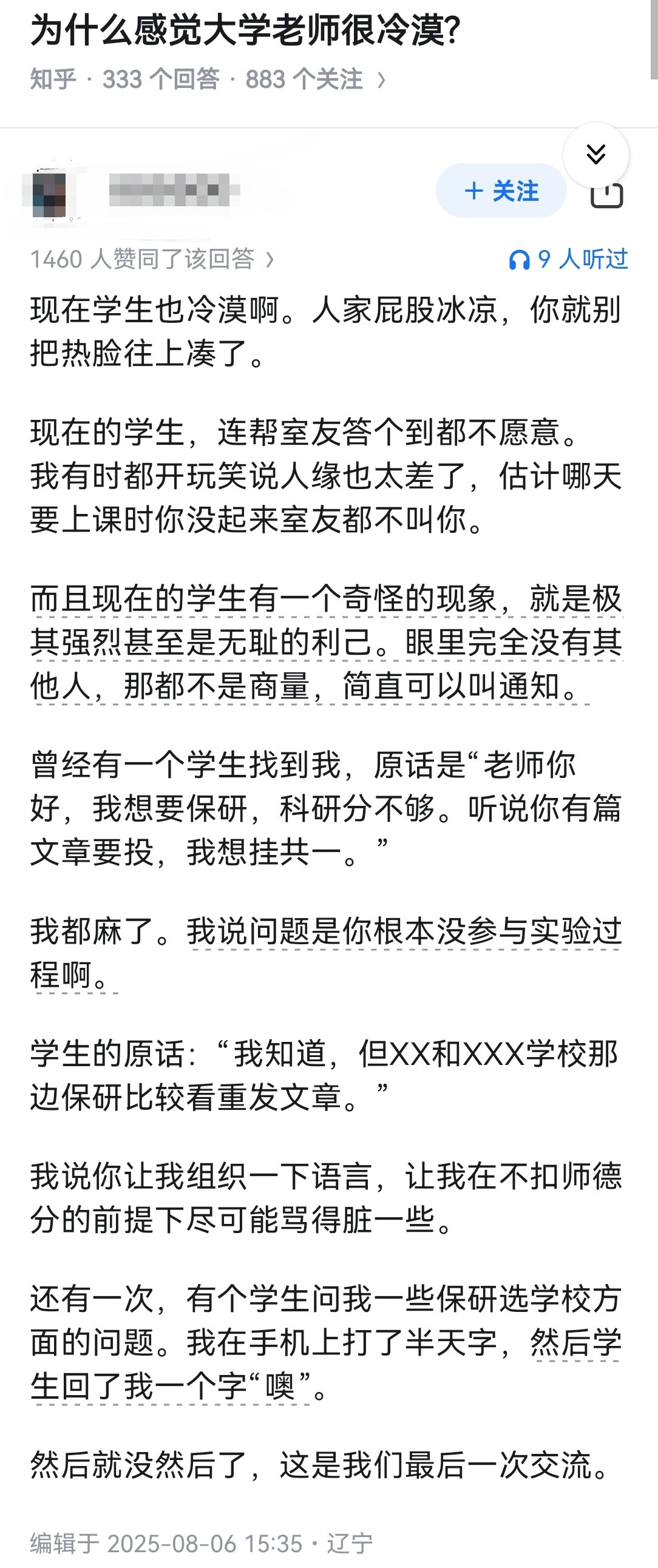母亲曾经资助了一个贫困学生,那人毕业后一直杳无音讯,前些日子忽然联系了我们。那天,电话铃声响起,母亲接起电话,听到那头传来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:“阿姨,是我,您还记得我吗?”母亲先是一愣,随即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,忙不迭地说道:“记得,记得,孩子,这些年你去哪了?” 母亲的旧木匣子里,总锁着一沓泛黄的信。收信人是“小宇”——十年前她结对资助的高中生。那时小宇家在山区,母亲每月从退休金里匀出三百块,一寄就是三年。 高考后小宇去了南方读大学,头年还偶尔来信,说兼职攒学费,后来渐渐没了音讯。母亲嘴上不说,却总在整理抽屉时,对着那张唯一的合影发呆——照片里的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,站在母亲身边,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。 上周三下午,阳光斜斜切过客厅地板,电话突然响了。母亲正眯着眼穿针引线,缝补我磨破的袖口,手一抖,针尖戳在指腹,沁出一点红。 “喂?”她含混地应着,没戴老花镜的眼睛凑向来电显示——陌生号码,归属地是深圳。 “阿姨,是我,您还记得我吗?”那头的声音有点闷,像蒙着层水汽,却突然撞开了母亲记忆里的某扇门。 她握着听筒的手指不自觉收紧,指节泛白,目光扫过茶几上刚泡好的菊花茶——那是她总说“等小宇来了要泡给他喝”的茶叶。“小宇?”她试探着问,尾音发颤,“你是小宇?” “嗯!阿姨,我是小宇!”少年的声音陡然亮起来,带着点哽咽,“对不起阿姨,这几年……我没敢联系您。” 母亲的眼泪“唰”地掉下来,砸在蓝布围裙上,洇出一小片深色。她顾不上擦,忙不迭地追问:“孩子,你过得好不好?是不是遇到难处了?当年怎么突然不写信了?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,然后小宇的声音慢慢清晰:“大学毕业那年,我爸突然脑溢血,家里欠了债,我打三份工还债,后来创业失败两次,总觉得没脸见您——您当年说‘要堂堂正正做人’,我却混得灰头土脸,哪敢说自己是您资助过的学生?” 母亲忽然笑了,带着泪:“傻孩子,我资助你,是盼你有出路,又不是图你报答。你过得好,我就安心了。”她起身去找纸笔,老花镜滑到鼻尖,“快,把你地址给我,我给你寄点家里的腊肠,你小时候总说爱吃。” 挂了电话,母亲把写着地址的纸条小心翼翼放进木匣子,和那沓旧信并排躺着。阳光透过窗棂,照在“小宇”两个字上,像落了层暖融融的金粉。 我忽然想起,去年整理母亲衣柜时,见过她在日记本上写:“今天路过中学,看见穿校服的孩子,就想起小宇。不知道他现在在哪,有没有好好吃饭?”原来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,早被岁月酿成了无声的期盼。 人这一辈子,总有些善意像种子,播下去时未必指望开花结果,却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长成了能为你遮阴的树。 或许我们都该学学母亲——给别人多一点时间,也给善良多一点耐心。毕竟,不是所有的沉默,都是遗忘。
你说气不气人,我女儿一不小心读到了博士!博士女儿又一不小心呢,又给我找了一
【74评论】【56点赞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