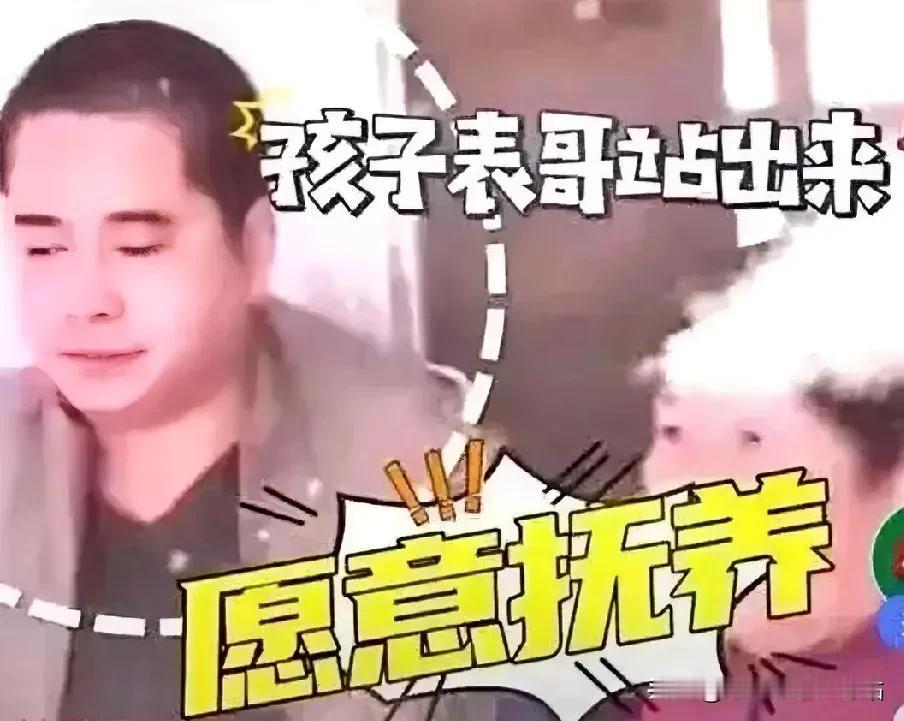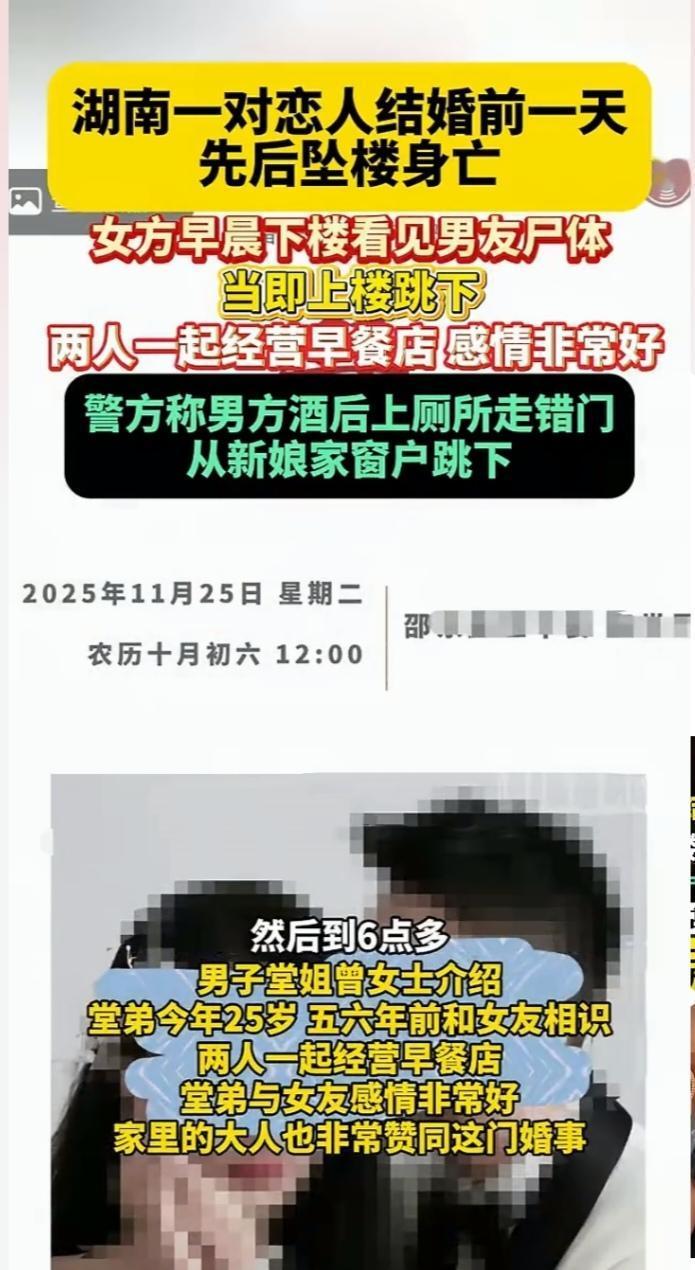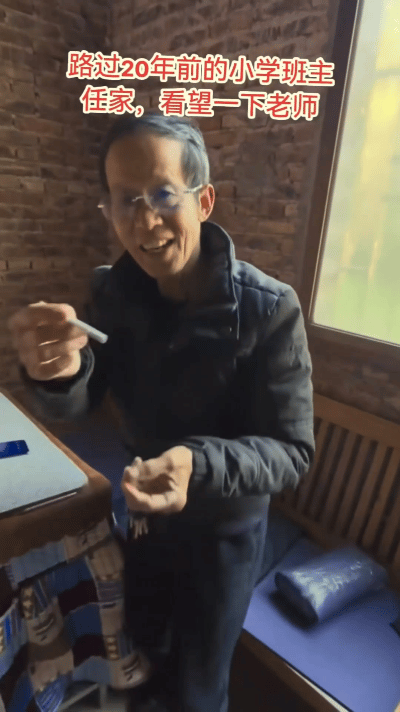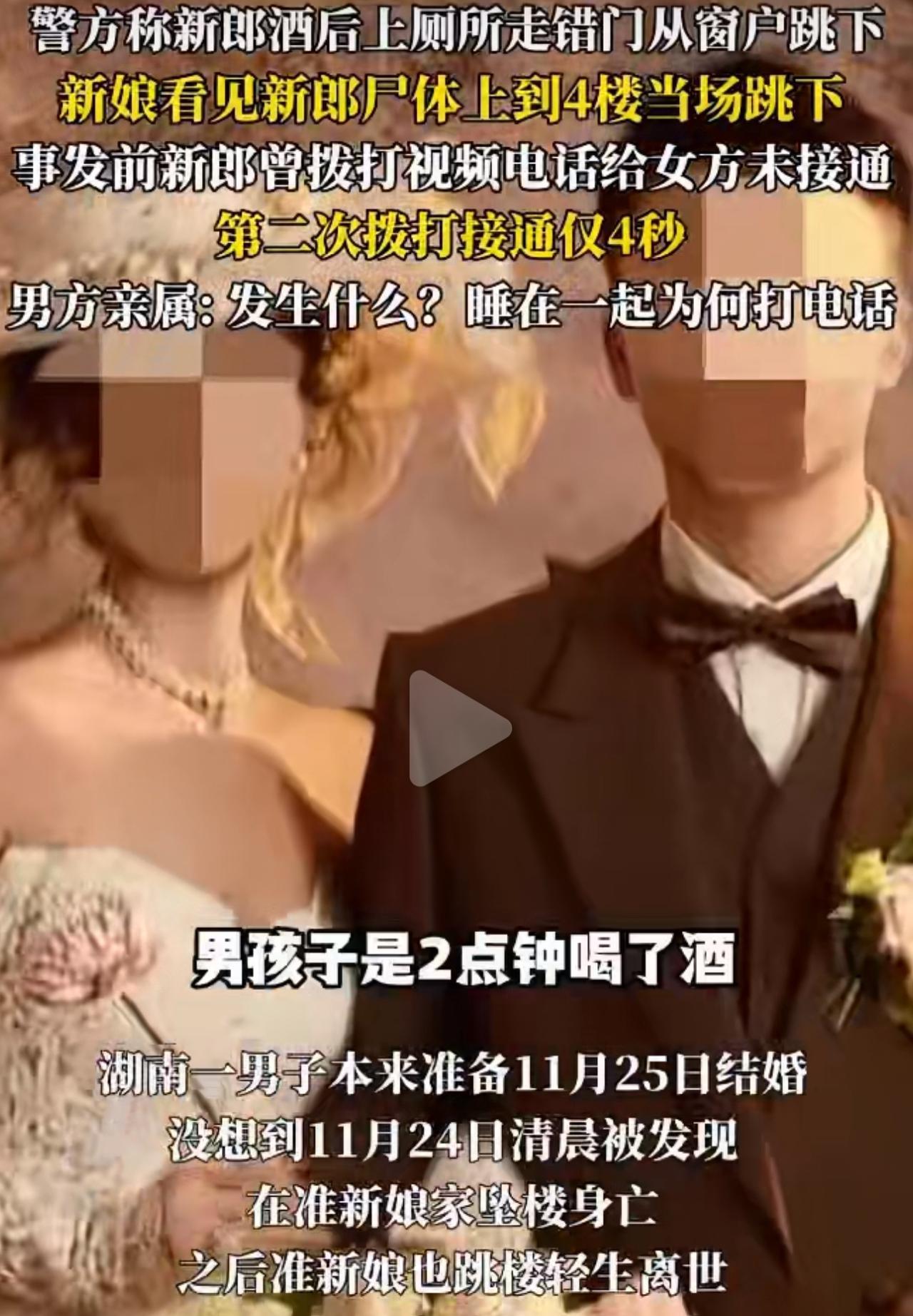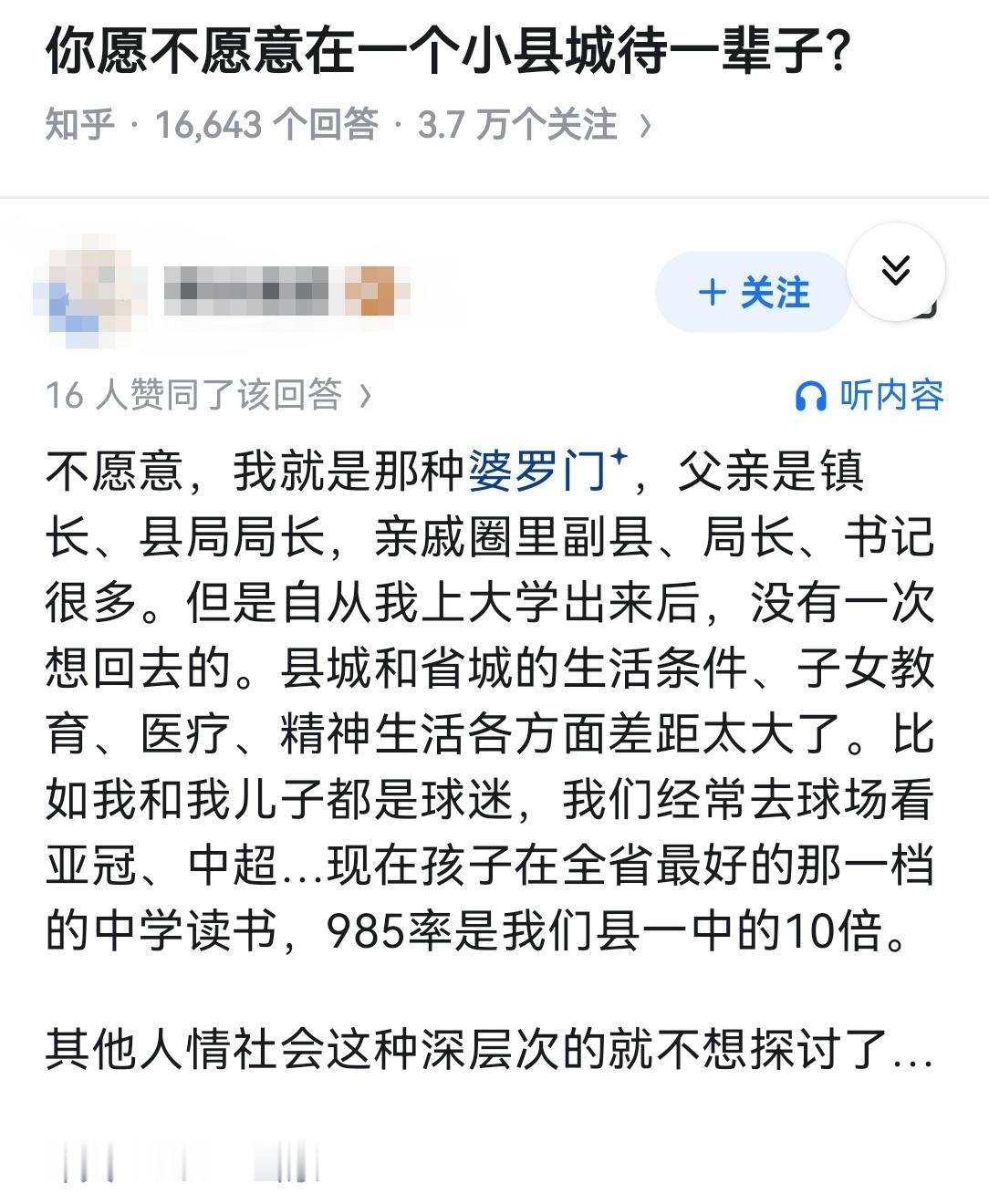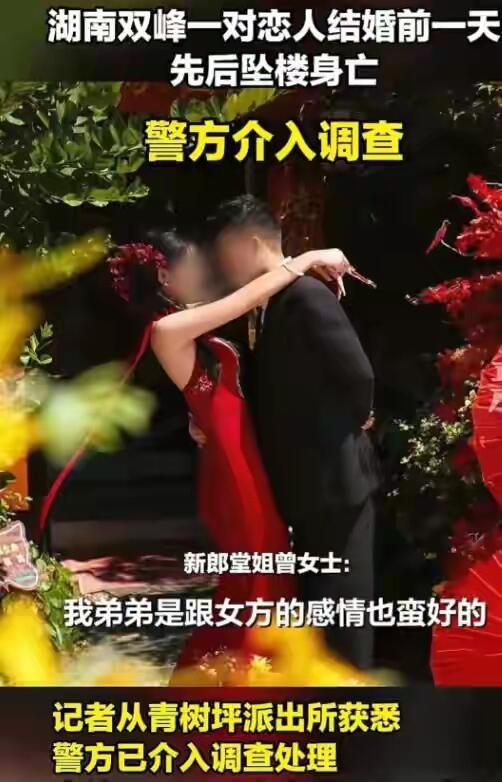1830年春,两江总督陶澍的夫人黄春兰,乘着蓝布小轿回湖南安化探亲。轿子行至县城外土路时,突然被个疯癫女乞丐拦住。女人嘶哑着嗓子叫骂:“黄春兰!你出来!都是因为你,我这辈子全毁了!” 黄春兰掀开轿帘一角,看清那人模样后,眼泪顿时涌了出来。 她轻声吩咐仆妇:“包五十两银子给她。” 而这个简单的举动,背后却藏着三十年的恩怨纠葛。 时间回到1798年,那天在黄家大院里,16岁的丫鬟春兰跪在黄老爷面前。 “老爷,让我替小姐嫁吧。“ 就在刚才,他还为悔婚的事发愁,陶澍这次乡试又落榜了,黄家不想把宝贝女儿黄德芬嫁过去受苦。 可悔婚又损名声,此时的他正左右为难。 而春兰的主动请缨,解了黄家的围。 她记得三年前被卖进黄家时,小姐黄德芬曾偷偷塞给她一块桂花糕。 这份恩情,她一直记在心里。 最后黄老爷也同意了。 洞房陶澍掀开红盖头时,春兰的心快跳出嗓子眼。 她扑通跪地,把替嫁的事全盘托出:“姑爷,我不是黄家小姐,只是个丫鬟……” 听到这话的陶澍沉默良久,最终吹灭喜烛:“睡吧,明日还要磨墨。” 而这一夜,春兰从丫鬟变成了陶夫人。 婚后的日子清苦异常。 但春兰毫无怨言。 每天五更起床包揽所有家务。 而且两人的感情也很和睦。 有年陶澍要进京赶考,连路费都凑不齐。 春兰连夜缝制六双布鞋、四件冬衣,拿到集市卖了十两银子塞给他:“路上小心。” 这次陶澍又落榜了。回家时正逢安化闹饥荒,米价飞涨,家里快揭不开锅。 是春兰掏出自己唯一的绣花手帕:“把这个当了,换点米。” 陶澍当掉手帕换回米,煮了锅粥。 “委屈你了。”陶澍有时会这么说。 春兰总是笑笑:“读书是正事,我这点辛苦算啥。” 其实陶澍何尝不知春兰身份?但他从不说破。 1802年,陶澍再次赴考,终于高中进士,被授翰林院编修。 就在喜报传来那天,安化县城炸开了锅。 陶家寒门出了个进士,简直是惊天大事。 乡亲们挤满小院,春兰忙着招呼,脸上是掩不住的笑。 赴任北京前,春兰收拾行李。 她拿起又放下,最后只带了几件旧衣和那卷做鞋底的旧布。 而陶澍看见,默默把她的嫁衣也塞进箱子。 但是在京城生活并不轻松。 为陶澍在官场以正直闻名。 1809年,朝廷推行“捐纳进阶”制度也就是所谓的花钱买官,陶澍独自上疏反对,言辞犀利。 同僚都劝他别得罪人,春兰却温壶酒说:“你做得对,别往心里去。” 此后陶澍官运亨通,从户部主事做到江南道监察御史,1830年升任两江总督,管辖江苏、江西、安徽三省。 就在到任第三天,陶澍就废除运河税卡三十六处,每年为百姓省下160万两银子。 他还整顿漕运、开办铁厂、查办贪官,江南百姓送匾称赞他“不避权贵,敢言直行”。 然而就在陶澍平步青云时,真正的黄家小姐黄德芬,命运却急转直下。 当年黄德芬嫁给了当地盐商吴家公子。 虽说婚礼风光无限,可惜好景不长,吴家因私运盐被查,公子死于狱中。 而黄德芬二十岁守寡,家产被族人霸占,沦落到住破屋、靠变卖首饰度日。 1830年春天,黄春兰回乡省亲的官轿行至安化城外,遇到了疯癫的张翠儿。 只见这个女人枯发如草,嘴里嘶喊着“偷人生的贼”。 仆妇要赶人,但是被黄春兰拦住。 她掀开轿帘,看见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,尽管岁月沧桑,她还是一眼认出了那是当年待她不错的小姐。 “包五十两银子给她。”黄春兰含泪吩咐。 银子递过去时,张翠儿愣了愣,一把抢过银包紧紧抱在怀里:“我的钱……该是我的……” 黄春兰坐在轿里,对侍女说:“回头打听下,把她送到附近善堂,托人好生照看。” 侍女不解:“夫人,她那样骂您,您怎么还对她这么好?” 黄春兰望着窗外田野:“她也是个苦命人。 再说,陶大人常说,做人要存善心,能帮一把是一把。” 后来陶澍知道这事,只叹口气,让春兰多接济善堂。 而张翠儿在善堂照看下,疯病时好时坏,再也没机会拦轿骂街了。 晚年的黄春兰常对子孙说:“人啊,得认命,但不能认输。” 她始终保持着简朴习惯,衣服自己缝,饮食简单。 1839年,陶澍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,而黄春兰为他守孝三年,不穿新衣,不戴首饰。 《清史稿》称陶澍“廉明谨正、恪守家风”,但是却未提春兰名字。 族谱中只简单写着:“黄氏,配陶公。” 而那个曾叱咤一时的黄家,早已没落无声。 黄老爷至死不知,他当年眼中的“投资”,竟如此天差地别地改变了两个女人的命运。 黄春兰的故事,在安化民间口耳相传。 老人们说,这叫“丫鬟的命,夫人的运”。 但细想下来,春兰的幸运并非偶然,她的善良、坚韧和付出,才是真正改变命运的关键。 有时历史就是这样,它不总是记载王侯将相,也会在某个寻常午后,通过一顶蓝布小轿和五十两银子,告诉我们关于人性和命运的最朴素道理。 主要信源:(《郎潜纪闻》《清史稿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