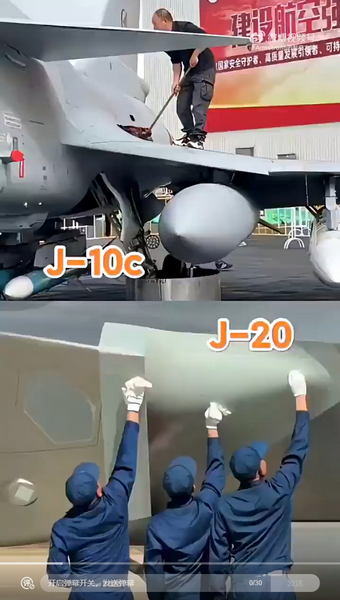村长和妇女主任到城里办事,办完事天色已晚,没有赶上回村的班车。两人商量找一个旅馆住一晚,到了旅馆,前台的小姑娘问:“二位住几间房?”村长看了眼妇女主任,先开口说:“两间吧,各住各的,方便。” 妇女主任跟着点头:“对,这样省心,回头村里问起来也清楚。” 小姑娘低头查了查电脑,抬头说:“不好意思啊叔姨,今天住的人多,就剩一间双床房了,其他旅馆我刚帮你们问了,附近几家都满了,这时候进城办事的、串亲戚的多,晚了确实不好找。” 末班车的影子早没了,村口那棵老槐树的轮廓在手机屏上晃了晃——村长和妇女主任站在县城汽车站门口,风卷着尘土往裤腿里钻。 “找个旅馆吧。”村长摸出烟盒,空的,捏扁了塞进裤兜。 妇女主任把帆布包往肩上提了提,“嗯,明早头班车回去,误不了给玉米地放水。” 旅馆的玻璃门刚擦过,映出两人的影子——一个头发花白,一个鬓角有根白丝,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。 前台小姑娘抬头,睫毛上还沾着睫毛膏,“二位住几间房?” 村长往妇女主任那边瞥了眼,妇女主任正盯着墙上的价目表,手指在“标准间”三个字上顿了顿。 “两间吧。”村长的声音比平时在村部开会低了些,“各住各的,方便。” 妇女主任跟着点头,“对,省心——回头二婶子问起来,也好说。” 小姑娘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,“叔姨,真对不住,就剩一间双床房了;我刚打电话问了隔壁三家,都满了——这两天城里开农资会,串亲戚的也多,晚一步就没地儿了。” 空气好像凝住了,妇女主任的帆布包带子滑下来,她没接,倒是问了句:“双床房?中间隔多宽?” 小姑娘比划了一下,“能过个人,叔姨放心,两张床呢。” 村长的喉结动了动,没说啥——谁不知道村里的闲话比蒲公英种子飞得还快?去年李会计帮王寡妇修水管,都被传成“半夜送鸡蛋”,更别说他和妇女主任共处一室。 可眼下,除了这间房,还有哪儿能落脚?总不能在汽车站蹲一夜,妇女主任的膝盖一到阴雨天就疼,地上的凉气钻骨头。 小姑娘把房卡递过来,塑料壳子上印着朵褪色的玫瑰——302房,楼梯口第二间,热水管在墙里嗡嗡响,像村里开会时的老电扇。 双床房的两张床,中间隔着一张床头柜,上面摆着个掉漆的台灯;妇女主任把包放在靠窗那张床,拉开窗帘一角,“能看见汽车站的牌子,明早不用摸黑找路。” 村长坐在另一张床上,床板“吱呀”一声,他赶紧起身,“我去买包烟。” “别走远,”妇女主任从包里摸出个苹果,“我这儿有苹果,洗了吃。” 谁也没提“万一村里知道了”的事——可谁心里都跟明镜似的,村西头的喇叭每天早上喊政策,下午就传闲话,唾沫星子能淹死人。 灯开了两盏,村长靠在床头看手机,屏幕上是玉米价格的走势图;妇女主任把苹果切成两半,用纸巾包着递过去,“吃吧,自家树上结的,甜。” 后半夜,村长听见妇女主任轻轻咳嗽了一声,他把自己这边的被子往床沿拉了拉——月光从窗帘缝钻进来,在两张床之间画了条线,谁也没越过。 有些关系,就像这双床房的两盏灯,不用靠太近,亮着,就够了。 第二天头班车的引擎声在窗外响时,妇女主任发现村长的床铺上,被子叠得方方正正,像他每次在村部门口升国旗时那样——边角都对齐了
江启臣再度上演“内斗”戏台上的“醒世恒言”。近来,国民党支持率略升,从21.9%
【23评论】【17点赞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