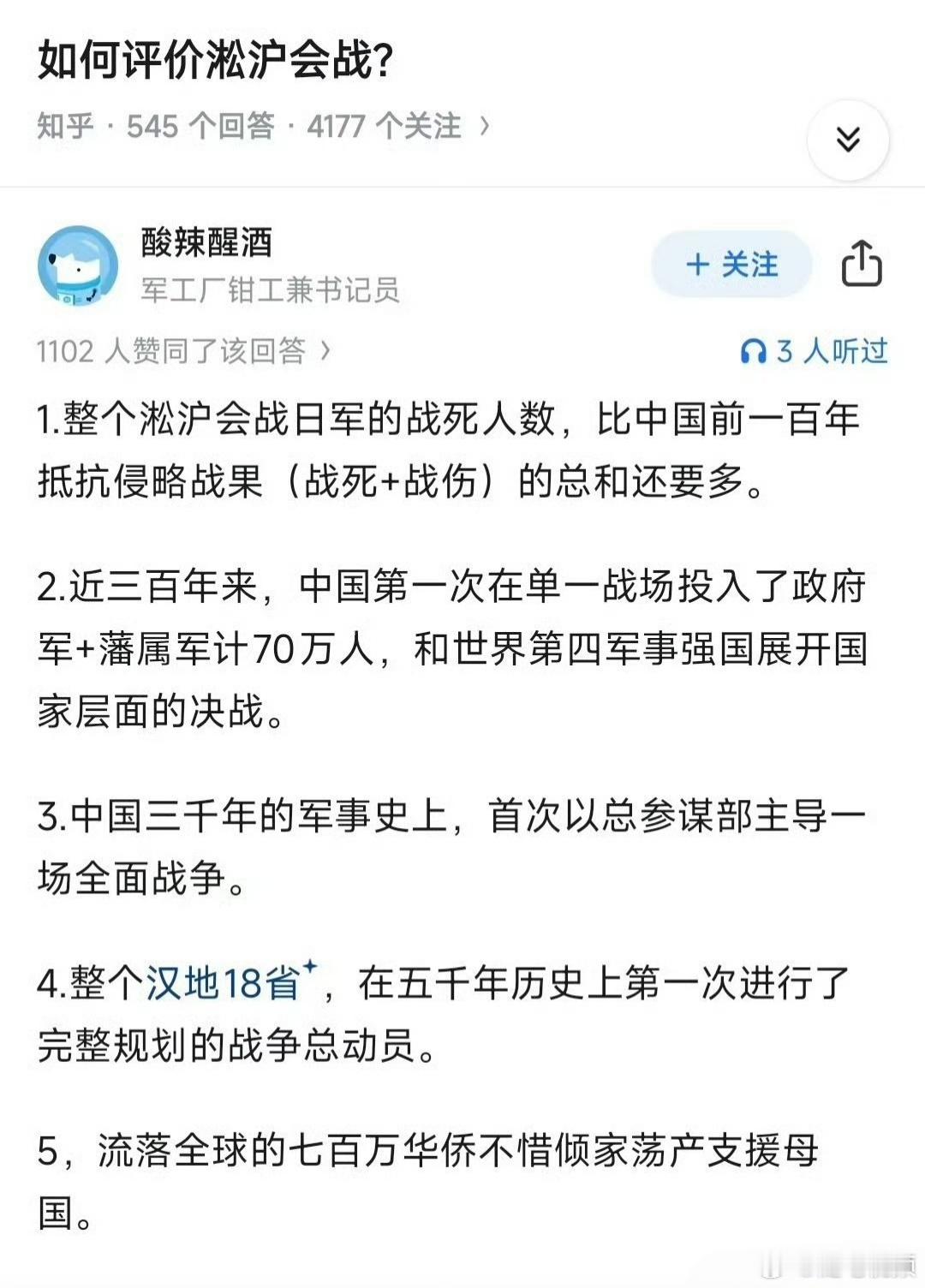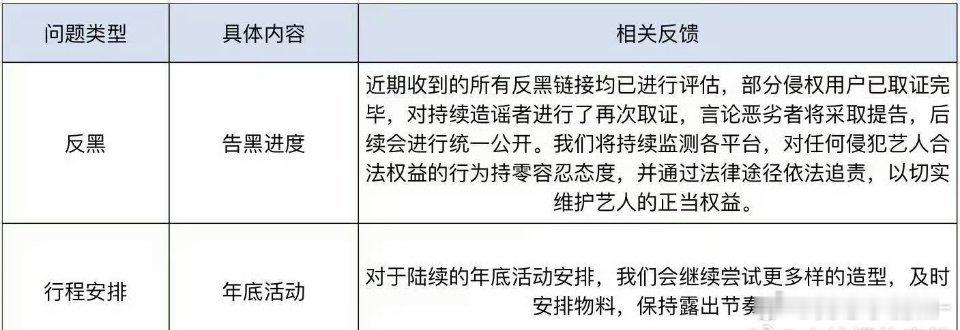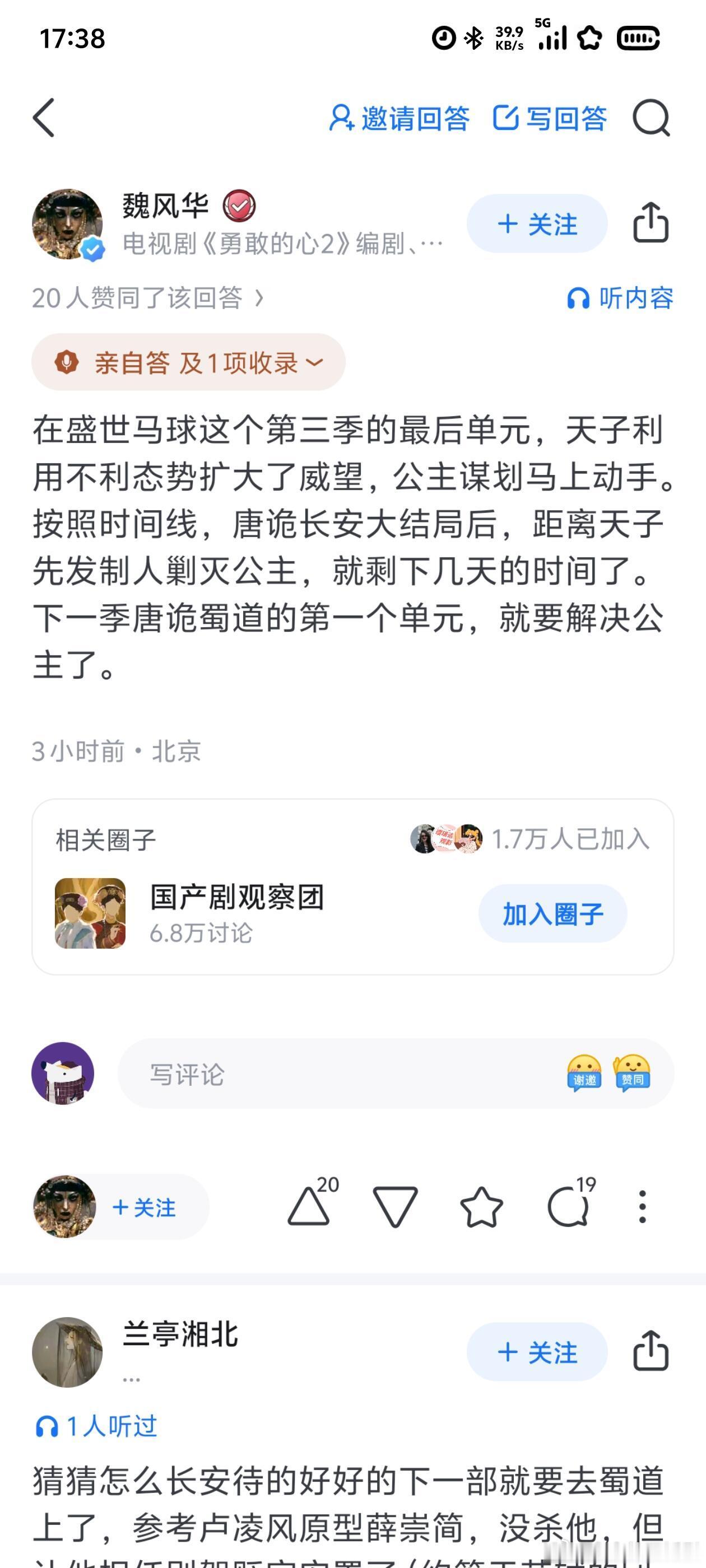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:“我父亲是侵华日军,我从不吃中国菜,因为我不配,我也不生小孩,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。这样的血脉,必须要在我这一代终结。” 作为享誉全球的日本作家,村上春树有个让人费解的怪癖:只要踏上中国的土地,不管接待规格多高,面前摆着多么诱人的山珍海味,他都要把自己关在酒店房间里,默默吃随身携带的日本罐头。 外人觉得荒谬,可对他来说,这背后是难以言说的愧疚——他觉得自己不配吃中国的食物,因为父亲曾是侵略中国的日军,而他的血管里,流淌着侵略者的“恶魔血液”。 这份对出身的深深厌恶,让他做出了极其决绝的决定:终生不要孩子。 在他看来,生孩子不是生命的延续,而是暴戾基因的复制。那段沉重的血脉诅咒,必须在他这一代彻底画上句号。 这一切的根源,都在他那位有着僧侣与士兵双重身份的父亲——村上千秋。 童年时的早晨,村上春树总被沉闷的诵经声唤醒。身为语文教师的父亲,每天都会跪在佛龛前,对着先祖虔诚祈祷。 他曾天真地问父亲为何诵经,父亲只含糊地说是为了“超度亡灵”。 直到后来,从那些关于战争的只言片语中,他才拼凑出真相:那些经文,是为了父亲在中国战场杀害的亡魂而念。 少年时的村上春树,心里满是恐惧。父亲曾说起“中国士兵明知要被砍头,却毫不畏惧”的残酷回忆,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扎进了他的潜意识。 成年后,这种精神上的撕裂变成了激烈的父子对峙。他渴望从父亲口中听到对侵略战争明确的反省,可换来的只有上一代人的沉默与回避。 在良知与亲情的拉扯中,他说出了“断绝关系”的话,父子俩从此决裂二十年,直到父亲去世,也没能完全和解。 父亲的离世,并没有驱散他的恐惧,反而让他更迫切地想要查清真相。 年过花甲的村上春树,花了五年时间,像侦探一样翻查父亲的服役记录,走访父亲当年的战友。 他最害怕的,是证实父亲参与过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。 最终的调查结果让他在这个具体的时间点上松了口气:父亲是1938年8月才抵达中国的辎重兵,错开了南京大屠杀。 但他在父亲泛黄的日记本里,看到了父亲记录处决战俘时的心理挣扎,还有刺杀手无寸铁平民的文字。 那根刺,终究还是没能拔出来。他这才明白,父亲每日清晨的诵经,是一个刽子手试图在受害者的血泊中,寻找一丝灵魂的救赎。 既然血脉无法清洗,村上春树就把手中的笔变成了手术刀,一次次刺向日本社会极力掩盖的战争毒瘤。 2019年,他在《文艺春秋》发表随笔《弃猫》,不顾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传统,把父亲参与杀戮的过往层层摊开给公众。 在那个习惯模糊战争性质、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日本舆论场里,他的行为无疑是一种“叛逆”。 这种反骨早就藏在他的小说里。《奇鸟行状录》中,他描述了日军把人扔进井里投掷手榴弹的残暴; 《刺杀骑士团长》里,他用大篇幅书写南京大屠杀,揭露日军砍杀俘虏、尸体填满长江的惨状,更驳斥了日本右翼纠结“遇难人数”的无耻。 他直言,不管是40万还是10万,杀害平民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。 这样毫不留情的揭露,让他成了日本右翼的眼中钉,“卖国贼”“间谍”的谩骂从未停歇,甚至有人在他住所外进行威胁抵制。 但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从未退缩,正如他所说:“一滴雨水有其历史,也由于那段历史,即有着继承一滴雨水的责任。” 他用近乎自虐的方式,独自背负起家族乃至民族的历史债务。哪怕这份债务本不该由他独自偿还,他也要站在寒风中,用文字和斩断的血脉,为那个试图遗忘历史的社会,立起一块永不磨灭的警示牌。 他不恨自己的国家,恰恰相反,他在用最痛切的方式爱着它——哪怕这意味着,他要在无尽的赎罪之路上,做一个永远没有后代的独行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