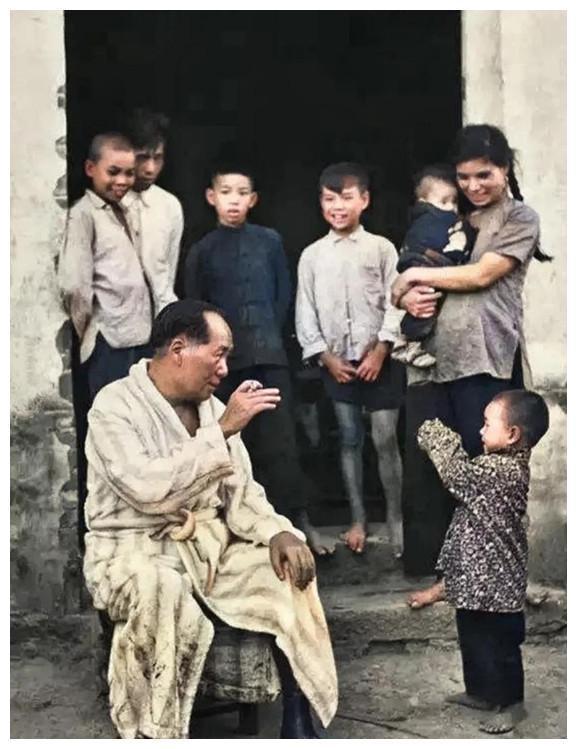看到主席写的沁园春雪后,有人说:“我终于明白那天在重庆为何一败涂地。我们是在作词,他是在开创时代。我们用墨写字,他用血与火写字。” 第一章 黄河冰渡 一九三六年二月,陕北袁家沟。 毛主席踩着深及脚踝的积雪,登上高坡。 连日行军,布鞋早已被雪水浸透,他却浑然不觉。 放眼望去,千里沟壑尽覆银装。 黄河如一条被冻住的巨龙,在悬崖下凝滞不动。 突然,风卷起雪沫,阳光下,连绵的群山仿佛扭动起来—— 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”他喃喃自语,“欲与天公试比高。” 警卫员小陈递来军用水壶: “主席,喝口热水吧。” 他接过抿了一口,目光仍锁在天地交接处。 这支刚刚走过万里长征的队伍,此刻正面对着更凶险的棋局——东渡黄河,北上抗日。 身后是追剿的国军,前方是虎视眈眈的日寇。 “小陈,你看这山河,”他忽然开口,“像不像五千年历史的战场?” 年轻人怔住了。 他眼里只有行军的艰难,主席看到的,却是漫漫长卷。 那天夜里,在窑洞摇曳的油灯下,毛润之铺开糙纸。 墨迹在寒冷中迅速凝固,每一笔都像在战斗: 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... 他不是在写诗,是在熔铸信念。 当笔锋转到“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时,窗外传来战士操练的号声。 他搁下笔,知道这首词不是终点,只是一个开始。 第二章 雾都文战 九年后的重庆,雾锁长江。 柳亚子捧着刚刚发表的《沁园春·雪》,手指微微发抖。 他是南社巨擘,见惯文人笔墨,此刻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。 “这等气象...” 他对郭沫若说,“六朝绮靡,唐宋工巧,何曾有过这等胸襟?” 郭默然点头。 他们都是旧学里泡大的,懂得这首词的分量——不仅在于笔力,更在于它改写了文人看世界的角度。 国民党宣传部长陈布雷却嗅到了危险。 他召集了一群御用文人,在嘉陵江边的茶楼密会。 “绝不能让他独占文坛鳌头,”陈布雷敲着桌面,“诸位都是词坛名家,务必和他几十首,压过这股气势。” 一场特殊的围剿开始了。 《中央日报》连续刊发和词,有的讥讽“草寇妄评帝王”,有的贬斥“不守词律”。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,这些作品纵然字斟句酌,在格局上已输了彻底。 最受震撼的是蒋介石。 他问陈布雷: “这词真是他写的?” “是的。文体属旧词,气象却是新的。” 蒋沉默良久: “他的词比他的军队更危险。” 第三章 两种风流 在曾家岩周公馆,毛润之听着文化界对这场论战的汇报,只是笑了笑。 “他们还是在比谁的典故用得好,谁的格律更精严。” 他点了支烟,“可是先生们,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。” 他走到窗前,看着码头上扛包的苦力,街上游行的大学生: “秦皇汉武,唐宗宋祖,当然是一世之雄。可惜他们的‘风流’,终究是帝王将相的风流。而今天——”他的手指轻轻划过玻璃,“创造历史的是他们。” 柳亚子那一刻恍然大悟。 原来这首词最革命处,不在于骂倒古人,而在于把“风流人物”的定义权,从士大夫手中夺回,交给了每一个平凡的“今朝”儿女。 尾声 雪落无声 许多年后,当这首词被谱成歌曲传唱天下时,当年参与围攻的文人们早已散落四方。 其中一位在日记中写道: “我终于明白那天在重庆为何一败涂地。我们是在作词,他是在开创时代。我们用墨写字,他用血与火写字。” 而最初的手稿,一直保存在延安的档案馆里。 纸已泛黄,但“还看今朝”四个字墨色如新,仿佛还在等待每一个黎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