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2年的一天,18岁的山田喜美子站在53岁的张大千面前,脱下衣服,涨红着脸说:“先生,拜托了!”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“关注”,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,感谢您的强烈支持! 1952年的东京,空气里还带着战后重建的那种既忙碌又充满期待的气息。 在一间不算特别宽敞、但摆满了笔墨纸砚和卷轴的日式房间里,张大千刚完成一幅画的最后几笔。 他放下笔,揉了揉有些发酸的手腕,目光落在正在一旁安静整理画具的年轻女子身上。 她叫山田喜美子,十八岁,穿着素净的和服,动作轻巧得像只猫。 她是朋友介绍来帮忙照料日常的,做事仔细,话也不多。 起初,张大千只是觉得这姑娘手脚麻利。 但时间久了,他发现自己作画时,偶尔瞥见她专注看着画笔在纸上晕染开的眼神,那里面有种纯粹的、近乎崇拜的光,让他这个早已习惯赞誉的人,心里也会微微一动。 喜美子对这位来自中国的“千桑”,起初是敬畏多于亲近。 他名气太大了,是报纸上常常提到的大画家。 但相处下来,她发现这位大师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威严。 他会因为画坏了一笔像个孩子一样懊恼,也会在吃到合口的点心时眯起眼睛满足地笑。 他教她辨认不同的宣纸,告诉她墨分五色。 有一次,他需要画一个特定姿态的人物,环顾画室,最后目光温和地落在她身上,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请求她做个参照。 那一刻,喜美子的脸腾地红了,心怦怦直跳,但还是鼓起勇气,按照他的示意缓缓摆出姿势。 窗外的光线斜照进来,空气里飘着淡淡的墨香和若有似无的少女体香,那个下午的时间仿佛走得特别慢。 就是从那时起,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,在两人之间悄悄生了根。 然而现实的世界并非只有画室里的静谧时光。 张大千是有家室的人,他的夫人徐雯波是陪伴他经历风雨的伴侣。 关于喜美子,这个家庭似乎有一种东方式的、沉默的接纳与平衡。 张大千的生活如同他的画作,需要游历四方汲取养分。 不久后,他因事务和创作的需要,常常需要离开日本,后来更一度在巴西定居。 而喜美子,大多时候留在了东京。 距离并没有切断联系,反而让一种更古典的交流方式变得重要起来——书信。 张大千无论走到哪里,瑞士的山间、巴西的庄园、香港的旅馆,他总会抽出时间给喜美子写信。 信纸有时是精致的笺纸,有时只是普通的便条。 内容包罗万象: 今天见到了什么有趣的人,画了一幅自己还算满意的画,异乡的饭菜不合胃口,或者只是简单地问一句“东京的樱花该开了吧”。 他的字迹时而工整,时而飞扬,喜悦时墨色酣畅,思乡时笔触里也仿佛带着叹息。 这些带着他独特气息的纸片,跨越重洋,被喜美子像守护最脆弱的蝴蝶标本一样,小心地收藏在一个精美的桐木盒子里。 这些信和画,成了她平淡生活里最隐秘而华丽的宝藏,是她与那个广阔而精彩的艺术世界之间唯一的、真实的连接。 岁月就这么在墨香与等待中静静流淌了十多年。 张大千的信依旧会来,但间隔似乎慢慢变长了。 他年纪大了,身体也不如从前,远渡重洋越来越成为一件艰难的事。 喜美子从青春少女,慢慢走向中年。 她一直没有结婚,生活中似乎也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故事,那个桐木盒子里的世界,或许承载了她大部分的情感。 大约在六十年代的某一天,她收到了可能是最后一封措辞更为慎重、更像告别的信。 从此,大洋两岸,各自的生活轨道向着不同的方向延伸,交集渐渐淡去,终于隐没在时间的河流里。 2014年,喜美子老人去世。 在整理她的遗物时,那个保存完好的桐木盒子被打开。 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的信札和画作,让见多识广的古董商也为之震撼。 后来,这些珍贵的物品出现在拍卖会上。 当拍卖师报出“张大千致山田喜美子书札七十九通”时,现场响起了一阵低低的惊叹。 经过激烈的竞价,这些发黄的纸页最终以超过两千万元的价格成交,新闻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版面。 人们谈论着这个惊人的数字,惊叹于大师手泽的巨额市场价值。 但在数字和喧嚣背后,是两段具体的人生,一份持续了十多年的、静默而绵长的牵挂。 它不完全是轰轰烈烈的爱情,也超越了普通的知己之情。 那些信,是张大千除了那些煌煌巨作之外,留下的另一种“真迹”——一种更私密、更鲜活的情感真迹。 它们让我们看到的,不仅是一位画坛巨匠的侧面,更是一个在才华和盛名之下,同样渴望倾诉、需要陪伴、会思念也会惆怅的、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 这段往事,就像他画中一幅淡淡的小品,藏在宏伟的山水长卷之后,不经意间瞥见,却别有一番动人的韵味。 主要信源:(澎湃新闻——往事|张大千的东瀛之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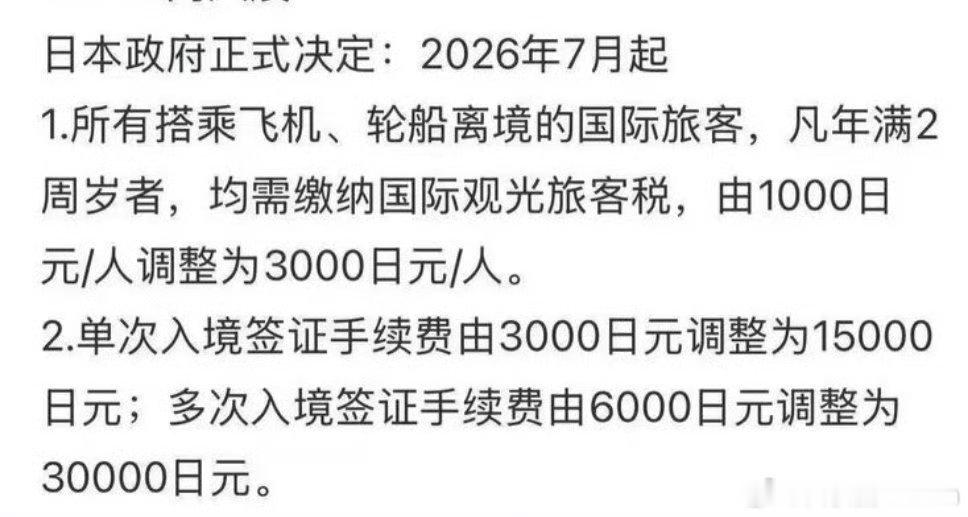


![厉害了我们的科学家!小老百姓吃喝全靠你们了[赞]1月6号央视报道,全世界都没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8248629507511653506.jpg?id=0)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