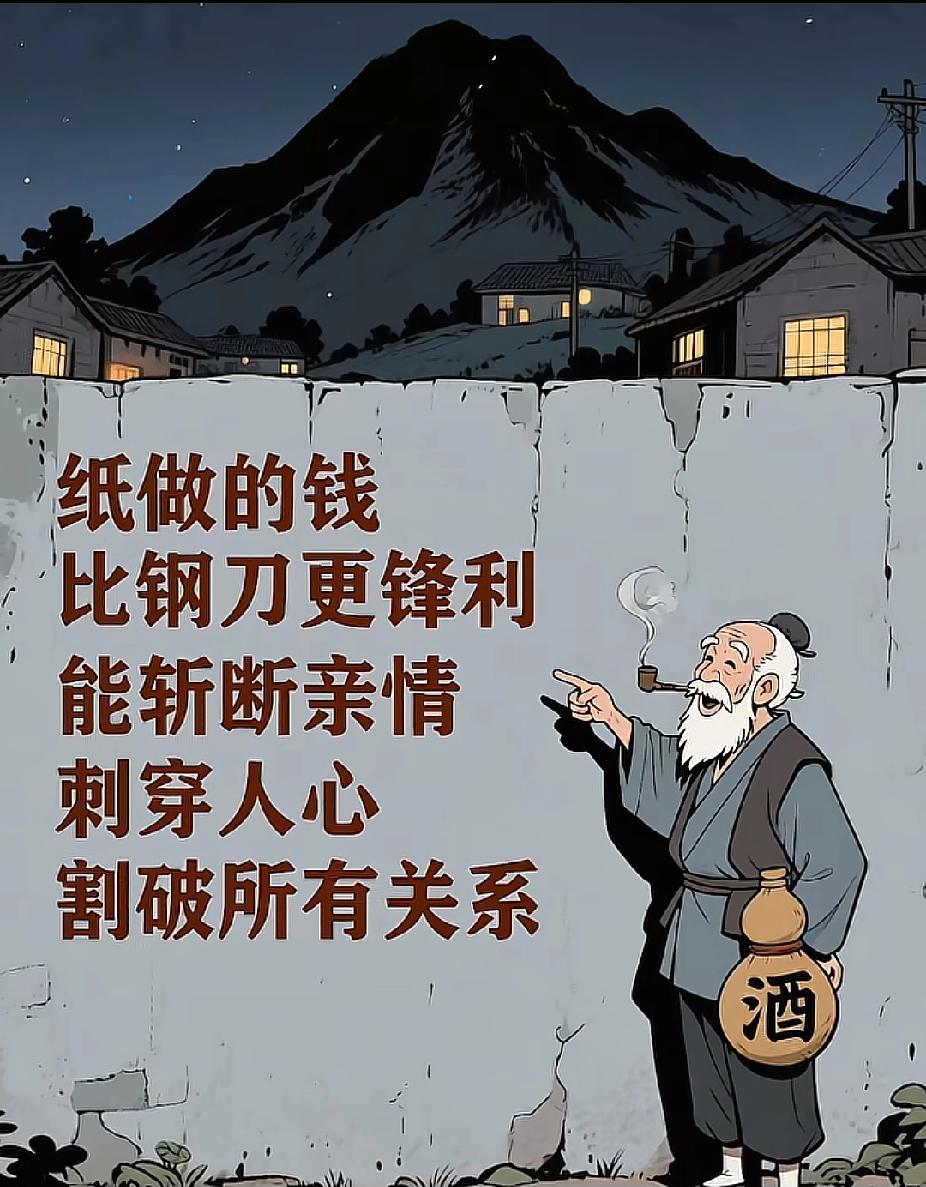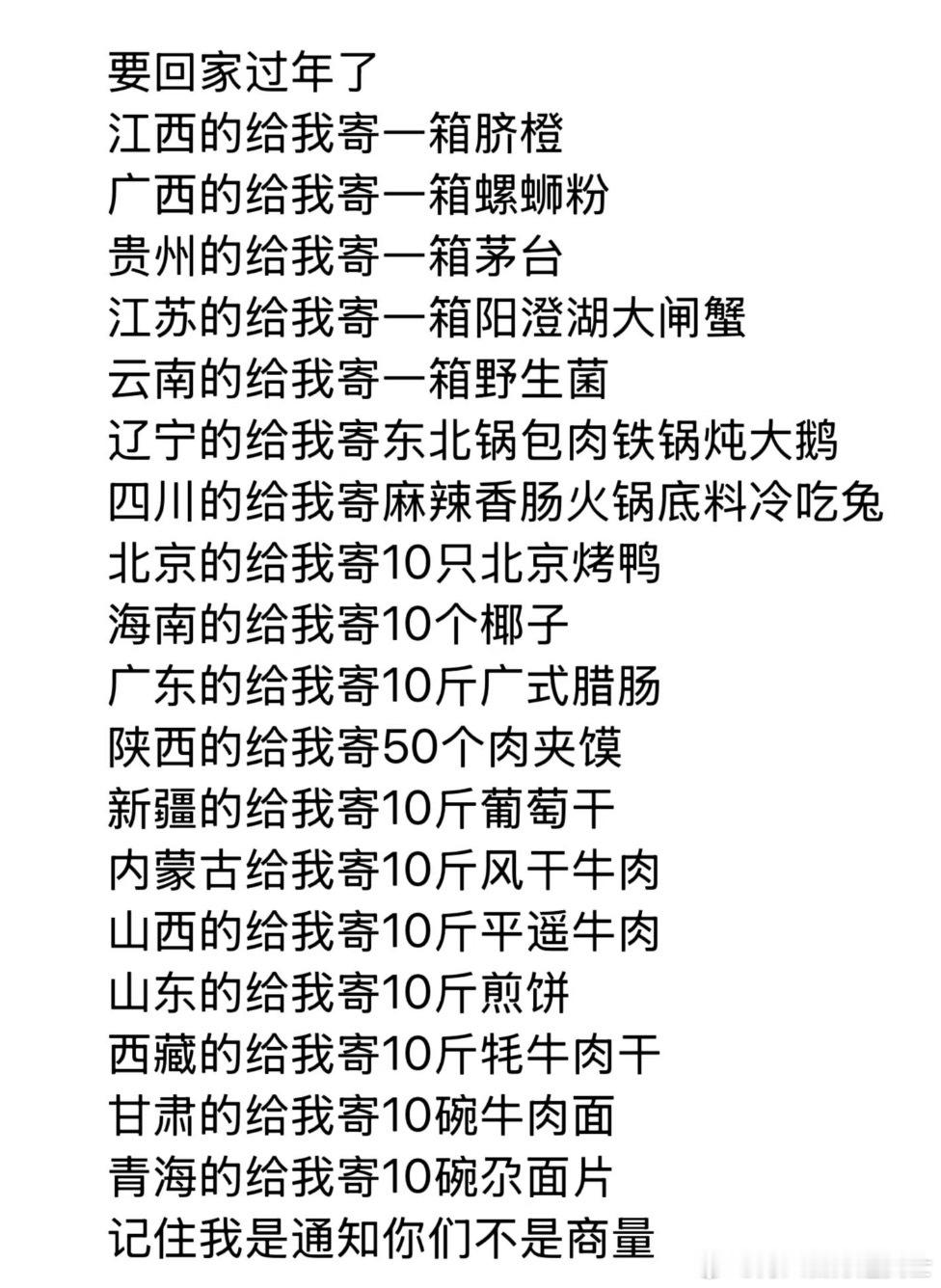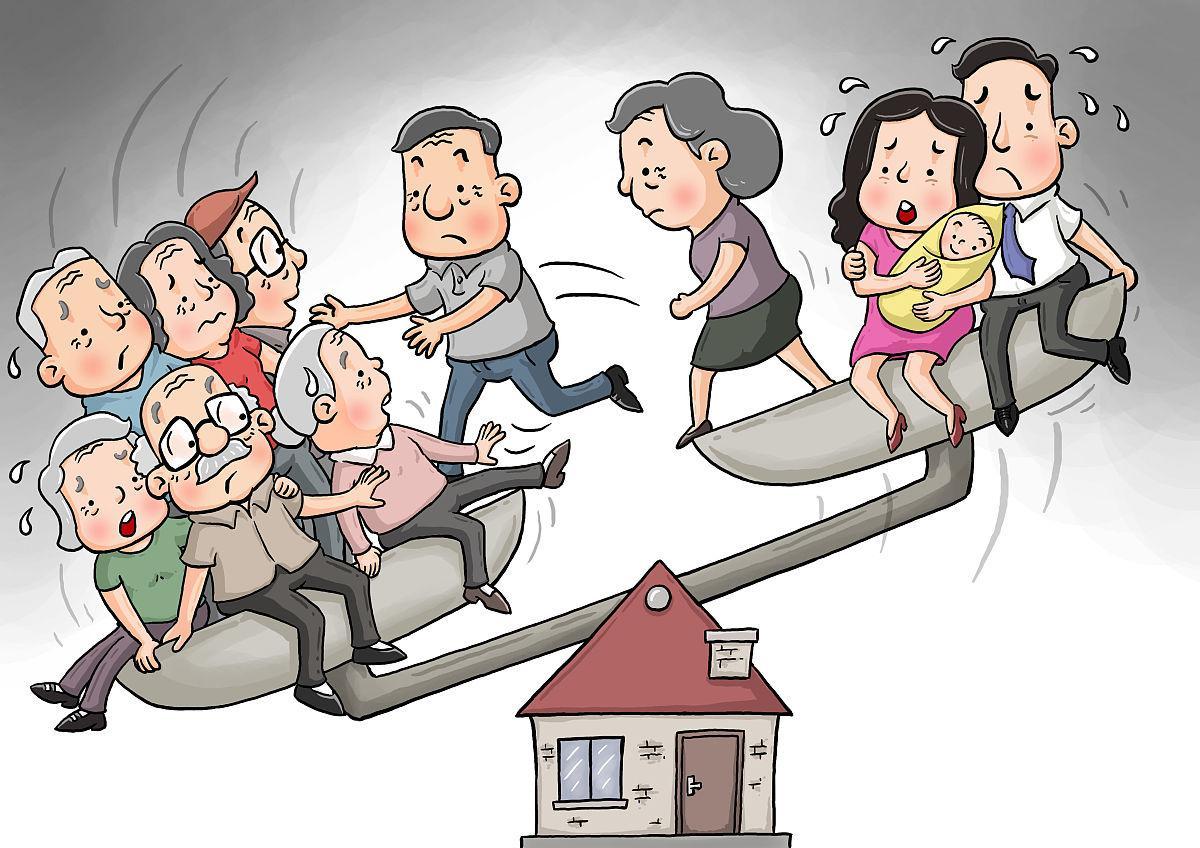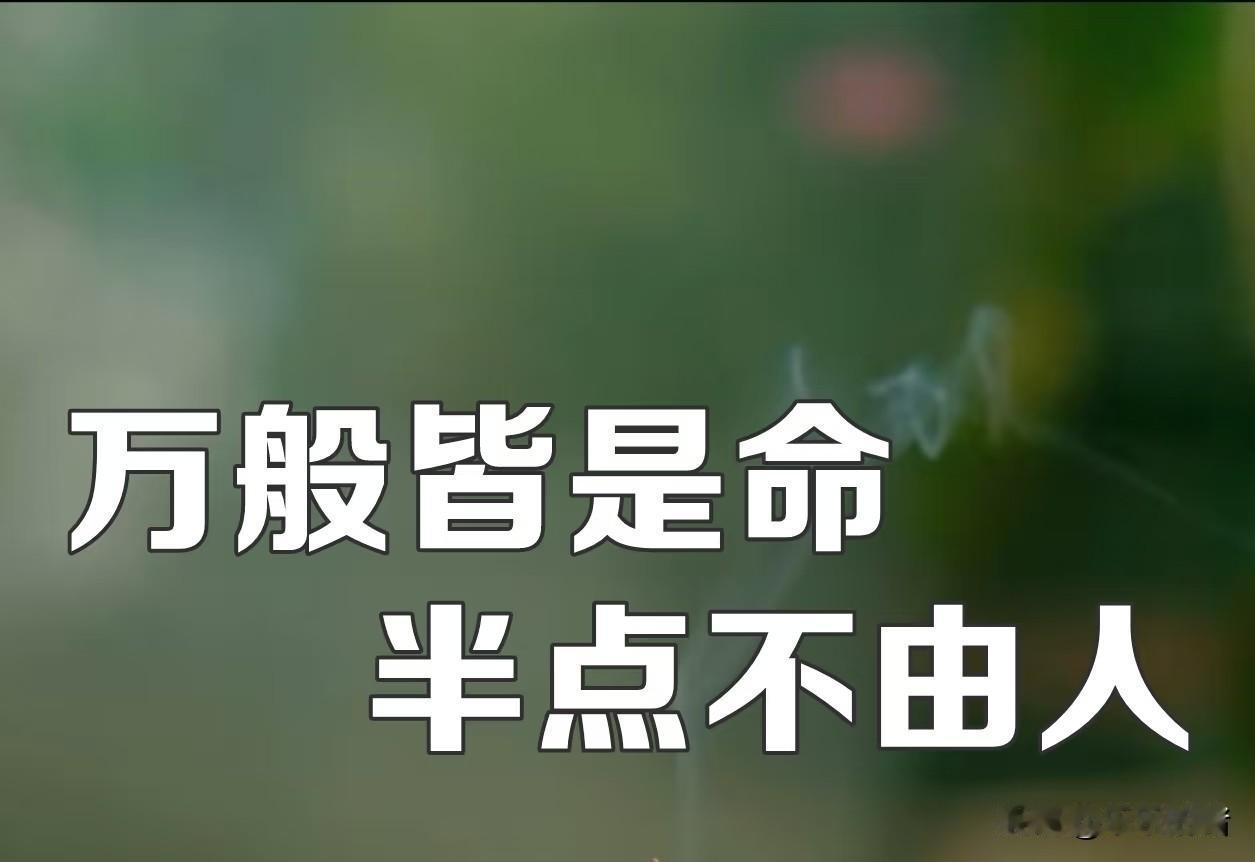“爸爸,卖掉小弟弟可以得到3000块钱。 深水埗的笼子间里,一家六口挤在不到十平米的空间。 铁丝网隔出的“房间”里,空气永远混着霉味和父亲工地上带回的汗味。 父亲每天凌晨四点就扛着工具出门,水泥袋磨破肩膀是常事,深夜回来时,鞋上的泥点能在地板印出一串模糊的脚印。 饭桌上永远是咸菜配白饭,弟弟总抢着扒拉碗里的米粒,陈小春那时最大的愿望,是让弟弟不用再啃咸菜根。 十三岁那年,他没再去学校。 跟着父亲去工地打杂,搬木板时手指被钉子划破,血滴在水泥地上,他咬着牙没哭父亲正扛着比他人还高的钢筋从身边走过,腰弯得像张弓。 那天在街头,两个男人的闲聊飘进耳朵:“收养个男娃,给三千块补偿。 ”他心里猛地一跳,三千块能买多少米?多少肉?弟弟去了好人家,就不用跟着他们饿肚子了。 耳光落下时,他尝到了血腥味。 但三天后的饭桌上,红烧肉的香气盖过了一切。 弟弟没坐在往常的位置,父亲把最大块的肉夹到他碗里,“吃,多吃点。 ”他低着头扒饭,肉堵在喉咙里,像吞了块石头。 后来他才知道,父亲那天揣着那三千块,在码头蹲了一夜,烟蒂扔了一地。 十六岁他离开家,在大排档端盘子,在后厨杂物间和老鼠抢地盘。 给客人倒茶时洒了水,被老板指着鼻子骂,他攥紧抹布没还嘴想起父亲扛钢筋的背影,这点委屈算什么。 直到看到无线舞蹈班招生,他光着脚在地板上转圈,汗水把地板洇湿一片,考官说“你这股劲,有点意思”。 伴舞的日子里,他给梅艳芳递过话筒,给张国荣整理过衣角,一场演出五十块,够买两斤肉。 后来组了组合,唱《失恋阵线联盟》,再后来演“山鸡”,红透半边天。 第一次带父母搬进九龙城的三居室,父亲摸着白墙,手背上的老茧蹭得墙皮沙沙响,“这辈子,值了。” 他想找弟弟。 托人查了无数档案,在演唱会后台对着镜头说“哥有钱了”,父亲却按住他的肩膀,“让他好好过吧。 ”父亲没说出口的是,当年送走弟弟时,他跟人签了协议,永不相认。 贫穷时被迫放手,富裕后不敢打扰,这是父亲用一辈子扛着的债。 现在他给儿子喂饭,总把鱼肉挑净刺再递过去。 小家伙把饭粒掉在桌上,他弯腰捡起塞进嘴里,像当年父亲捡起他掉的饭粒一样。 应采儿笑他“抠门”,他只是笑笑。 有些记忆不用提,比如那天没吃完的红烧肉,比如父亲转身时颤抖的肩膀,都化作现在给儿子擦嘴的纸巾,柔软又实在。
那年回老家奔丧,顺道看望一直种地的战友,那顿170块钱的饭,吃得我心里生疼。
【2评论】【2点赞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