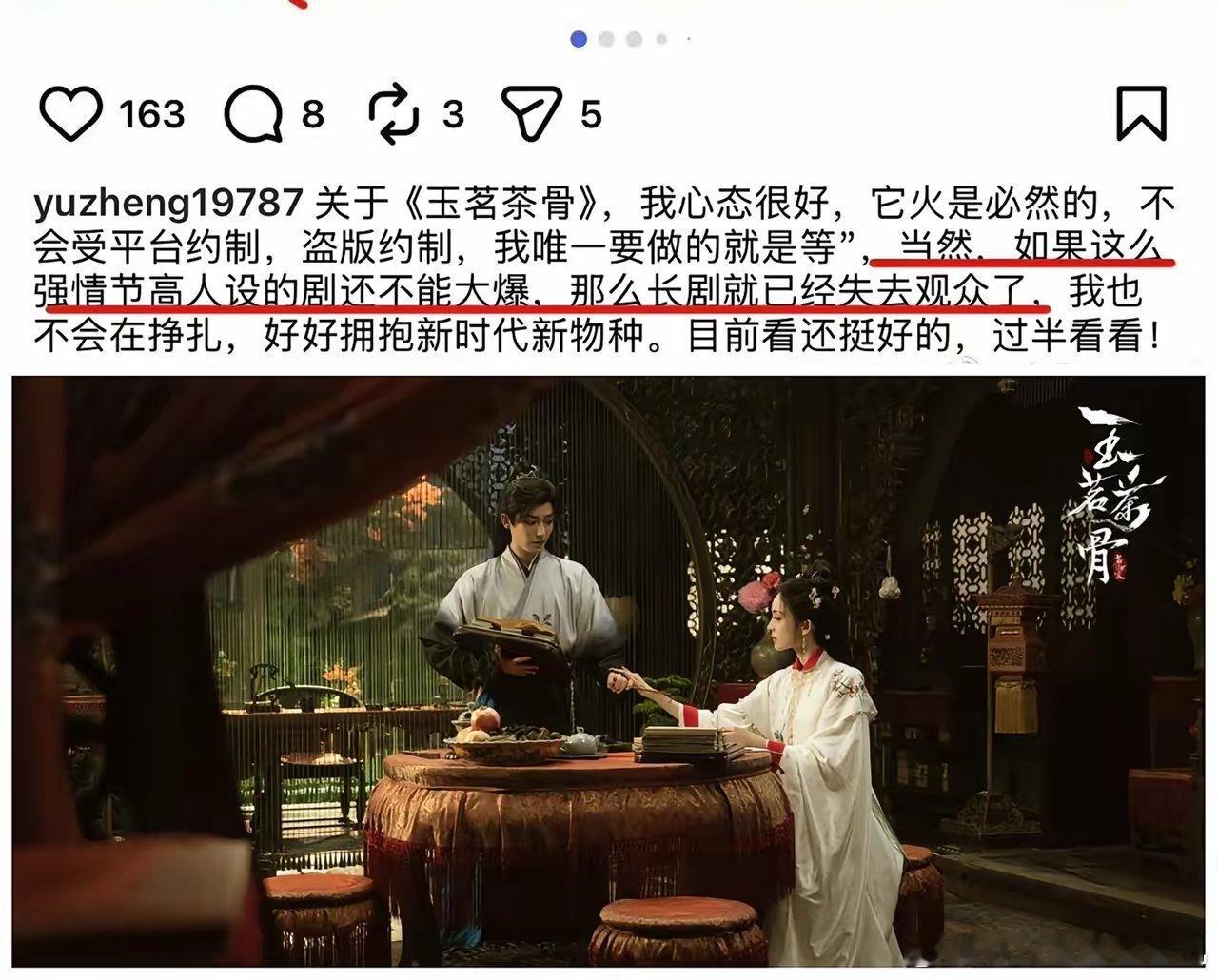侯明昊站在那儿,像一尊被精心打磨过的石膏像。谭松韵的灵动撞上去,古力娜扎的明艳映上去,都像水泼在石头上,流走了,没留下痕迹。 不是不努力。资源、搭档、机会,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,一件件递到他手里。他接住了,稳稳地,然后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个“表情指令”。笑是嘴角上扬的固定弧度,怒是眉心微蹙的标准模板。他把演戏变成了一套不出错的广播体操。 可观众要的不是标准答案。他们要的是活人。要的是角色在绝境里那一瞬间肌肉的抽搐,是狂喜时眼底一闪而过的泪光,是连演员自己都未必能完全控制的、属于“人”的意外。 于是两部大剧,成了两场盛大的浪费。顶流的能量,名导的光环,像昂贵的燃料投进一台设计精密的机器。机器运转无误,却点不燃任何人心里的火。人们看着他完美的侧脸线条,心里想的却是:可惜了。 这或许是最无声的悲剧。不是没有天赋,不是不被眷顾,而是所有的馈赠都被一套过于安全的程序锁死了。他像一个拥有顶级画具却只会临摹的孩子,世界把最斑斓的色彩给了他,他却交回一张工整的素描。 当“不出错”成了最大的错,那张无可挑剔的脸,会不会在某天照镜子时,感到一丝冰冷的陌生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