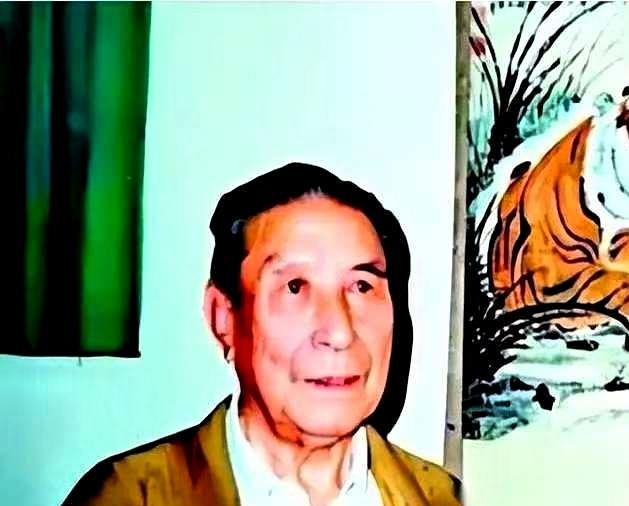1957年,傅作义到功德林看望陈长捷,陈长捷激动大喊:“你在北平谈判,让我坚守天津,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,我成了战犯,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!” 1957年的功德林,铁门一关,外面是新中国的喧闹,里面是旧账。 傅作义踏进监区,对面坐着的陈长捷,头发花白,眼神还倔。 一抬头就火气上来:“你在北平谈判,让我坚守天津,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,我成了战犯,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!”这一嗓子,把几十年的交情和一座城的下场,全吼出来。 这对老同学,故事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起头。 两个人一起挨骂跑圈,睡同一排大通铺,对着昏黄的灯写作业。 后来路子分开。傅作义打出几仗名堂,当上大员。陈长捷跟着阎锡山搞抗日,本想立功封赏,阎锡山疑心重,一纸命令把他的军权拿掉,说是“另有安排”,实际就是不信任,前途一下断了一大截。 人到山穷水尽,总会想起能托底的人。 陈长捷跑到绥远,找到已经成了“傅司令”的老同学。 在别人眼里,他是被上峰猜忌的旧将,在傅作义眼里,多了一层“同学”的情分。 傅作义看他会用兵,办事利索,就把他推到前线要紧岗位上,两个人在地图前摊开战局,从上下级变成掏心窝子的兄弟。 解放战争打响,天津的分量立刻不一样。 天津卡在华北要害位置,傅作义把这座城交给陈长捷守,是信任,也是把自己的一大块家底压上去。 城里修工事、挖战壕,调兵屯粮,大家心里清楚,这一仗躲不过。 偏巧这个节骨眼上,南京电报到了,蒋介石缺人,把主意打到这位老部下身上,要他南下护卫。 不少人觉得,这电报像一张“船票”,可以离开这座要打烂的城。 陈长捷回得很干脆,把电报一推,拒绝。他认的是傅作义交代的“守住天津”,觉得人在傅部帐下,就得先把这座城扛住。有人劝他换个活法,说解放军势头已成,真熬到城破再放下枪,迟早被扣上顽抗到底的帽子。 若能带部队起义,就是“有功”,待遇和前途都不一样。 劝归劝,他不接茬。 话说得很直:武器是军人的第二条命,放下枪是军人的耻辱,怎么能说丢就丢。 他认死理,也认“军人”这三个字。 傅作义的桌上,作战地图旁边已经压着谈判稿。他跟解放军代表接触,琢磨北平和平解放的路数。天津这块还得握在手里当筹码,他一面在谈判桌前斟酌字句,一面往天津发电报,让老部下坚守,把阵地顶住。 站在天津城头的陈长捷,对这些并不清楚,只知道自己手里有兵,背后有傅作义,只要里外配合,天津有希望守住。 他对部队有信心,对援军也有期待。 解放军总攻那天,炮火压上来,工事一段段被砸出缺口,战线越缩越短,盼着的外线部队始终没有出现。算盘打得再精,缺了一只手也难撑。 天津这座要害之城,只撑了二十九个小时,就安静下来。 城守不住,人也没投降。 陈长捷咬着“军人不丢枪”的那股劲,在新政权的账本上成了“拒不投降的战犯”。 天津解放之后,北平局势很快明朗,和平解放方案往前推得更快。傅作义成了“有功”的起义将领,又出现在新中国的水利部,忙着修水库治河流。有熟人半开玩笑问他,从总司令到一个部里的部长,落差是不是太大,心里会不会不平衡。 他说这些安排没有怨言,只是有一个人,对不起,就是陈长捷。 另一边,陈长捷被押进功德林。 他很快就听说傅作义因北平和平解放有功,不用改造,还能在新政府里任职,心里那口气一下子被点着。 嘴上骂他不仁不义,骂他拿兄弟当筹码,骂不过瘾,就绝食,用这种方式表示不服。身边的人劝,说时代已经翻篇,人活着,总得往后看几步。 他最后还是放下这股死劲,重新拿起碗筷,在高墙之内开始日复一日的改造生活。 时间拖到1957年,这场重逢就这样来了。 傅作义走进功德林,看上去像是来看望老部下,又像来还一笔旧账。 面对面坐下,空气里是尴尬,也是火星。 陈长捷猛地抛出那句“这辈子不会原谅你”,多年积在心里的话一股脑砸过去。傅作义一时间接不上,只能低着头听。 管教见气氛紧绷,只好出来打圆场,让两个人换个话题,聊聊从前的部队。 外头的人听说这件事,常拿“起义将领”和“战犯”这两个标签来对比,一个进了部委大楼,一个蹲在高墙之内。知道内情的人心里明白,这里有局势,也有性格,有布局算计,也有一根筋的坚守。 国家开始实行特赦制度,划出第一批特赦名单时,傅作义报上了陈长捷。手续走完,陈长捷从功德林走出,帽子轻了不少。 傅作义又帮着张罗,在上海给他落了户,让这位曾经的天津守将变成大城市里的普通居民。 从保定课堂上的学员,到绥远大帐里的搭档,再到天津城头那纸“死守”的命令,直到功德林铁门里的那声怒吼,两条人生被拧在一起,也被时代的大浪推开。 一个顺着潮水转了身,一个死守着“军人不能丢枪”的规矩,带着各自的选择往后半生走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