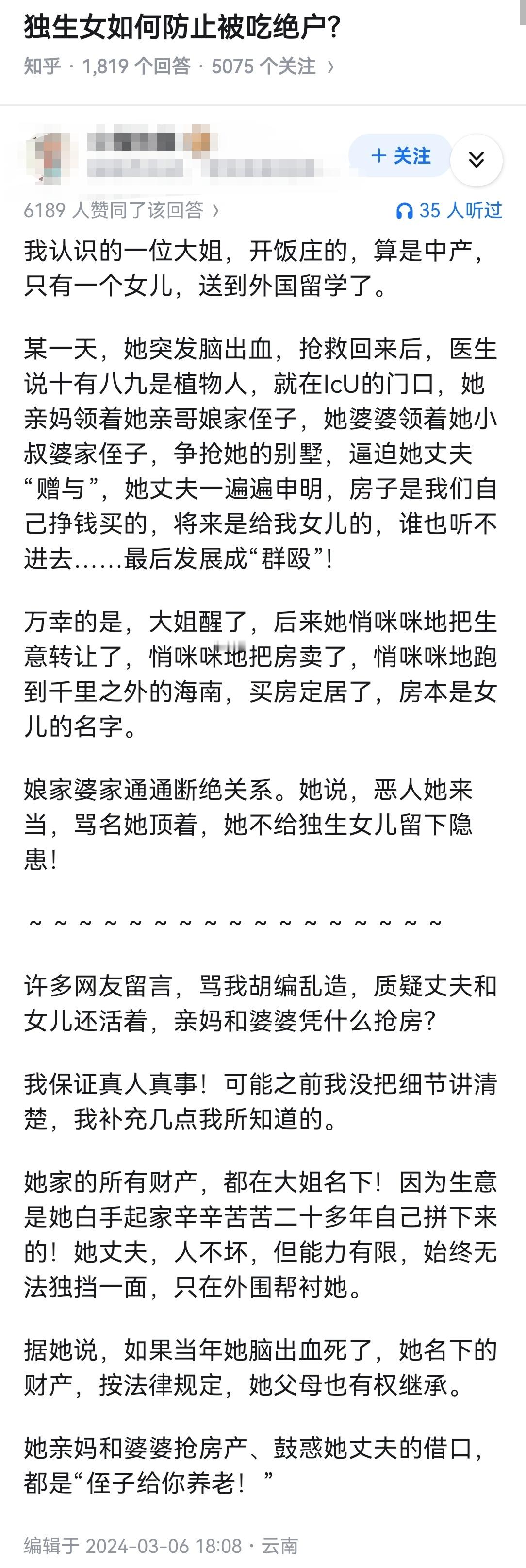1988年的那个春日午后,安徽乡下的土路上扬起细尘。 蔡国栋提着磨旧的皮箱站在自家老屋前,五十年没见的青砖院墙爬满了青苔。 门“吱呀”开了,刘金娥扶着门框站在那里,看见他身后跟着的女人和怯生生的女孩时,手里的竹篮“哐当”掉在地上,篮子里的鸡蛋滚了一地。 1935年的冬天,蔡家父母用两亩薄田作彩礼,把14岁的刘金娥娶进门。 新婚夜,15岁的蔡国栋蹲在院里抽完一整袋烟,说自己要去南京读书,这婚事不过是给爹娘一个交代。 刘金娥没接话,只是把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叠得方方正正,压在樟木箱底,箱角还放着他落下的一枚铜纽扣。 南京沦陷那年,蔡国栋跟着学校西迁,半道被抓了壮丁,后来成了国民党空军的地勤兵。 1949年部队撤退台湾时,他在基隆港给家里写过信,却再也没收到回音。 村里老人说,那几年海峡上的信,都沉在海里了。 刘金娥就守着那间老屋,土改时有人劝她改嫁,她说“蔡家总得留个人”;文革时红卫兵来抄家,她把蔡国栋的照片藏进墙缝,被推搡着按在泥地里也没松口。 在台湾的日子,蔡国栋不敢提大陆有妻。 三十岁那年经人介绍娶了台南姑娘林秀琴,生了一儿一女。 1987年听说能回大陆,他熬了半宿没睡,翻出珍藏的旧照片,照片上的刘金娥还是梳着辫子的模样。 出发前,林秀琴往他皮箱里塞了两盒台湾糕点,轻声说“见了面,好好说”。 重逢那天,蔡国栋张了张嘴,只说出“金娥,对不起”。 刘金娥看着他鬓角的白霜,又看看那个比自己还高的女孩,突然笑了,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。 “你走吧,”她弯腰去捡地上的鸡蛋,碎了的蛋清在泥里晕开,“蔡家的门,早就不是你的了。”我觉得,她不是不肯原谅,是五十年的等待里,早就把自己活成了蔡家的门,关上门,才能护住最后一点体面。 刘金娥后来把那枚铜纽扣缝在了贴身的蓝布衫上,蔡家老屋的烟囱再没为蔡国栋冒过烟。 海峡对岸的风,终究吹不散安徽乡下那个春日的鸡蛋香,也吹不散一个女人用半生守住的尊严不是等谁回来,是等自己能抬头说“我没输”的那一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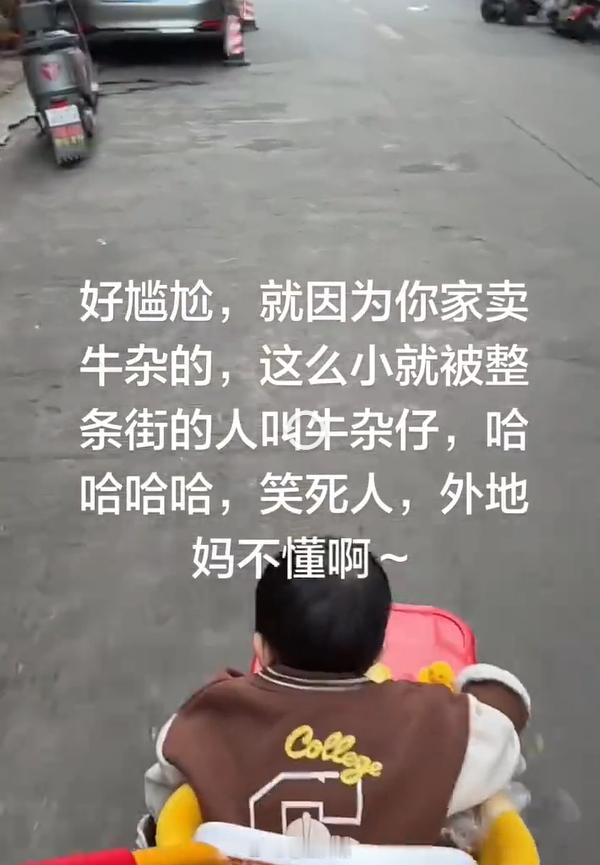
![中国的省会真空地带!!![捂脸哭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8874725193469365599.jpg?id=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