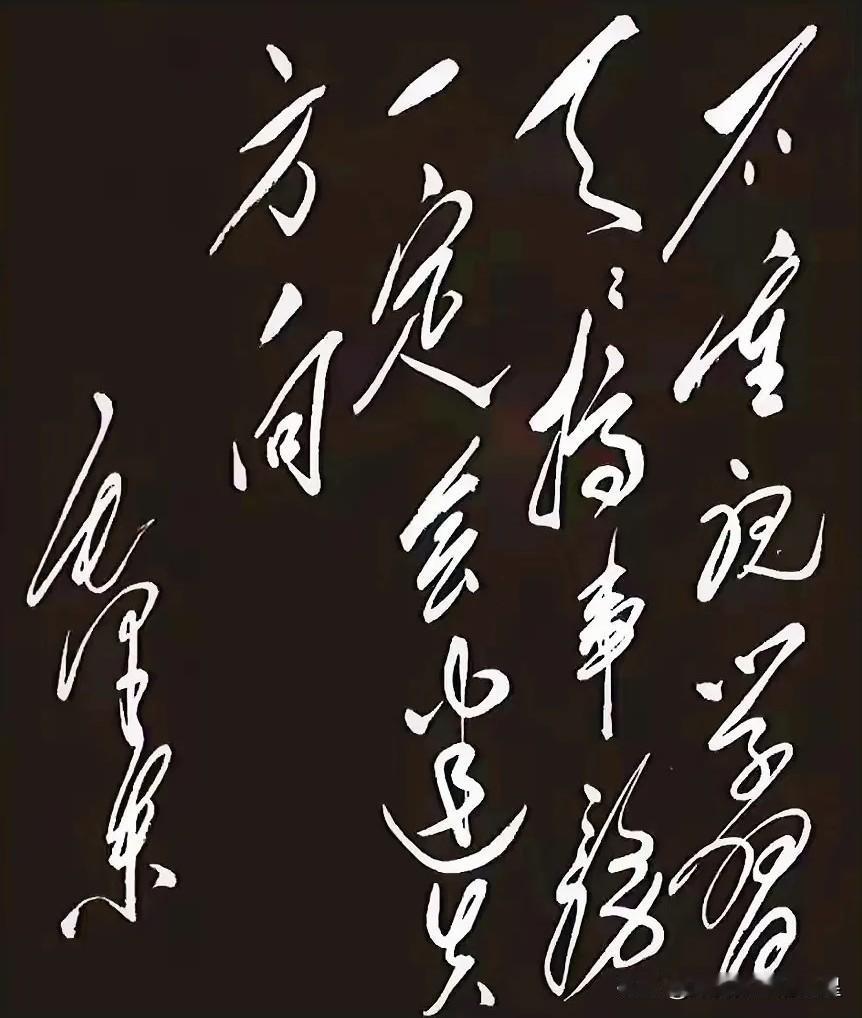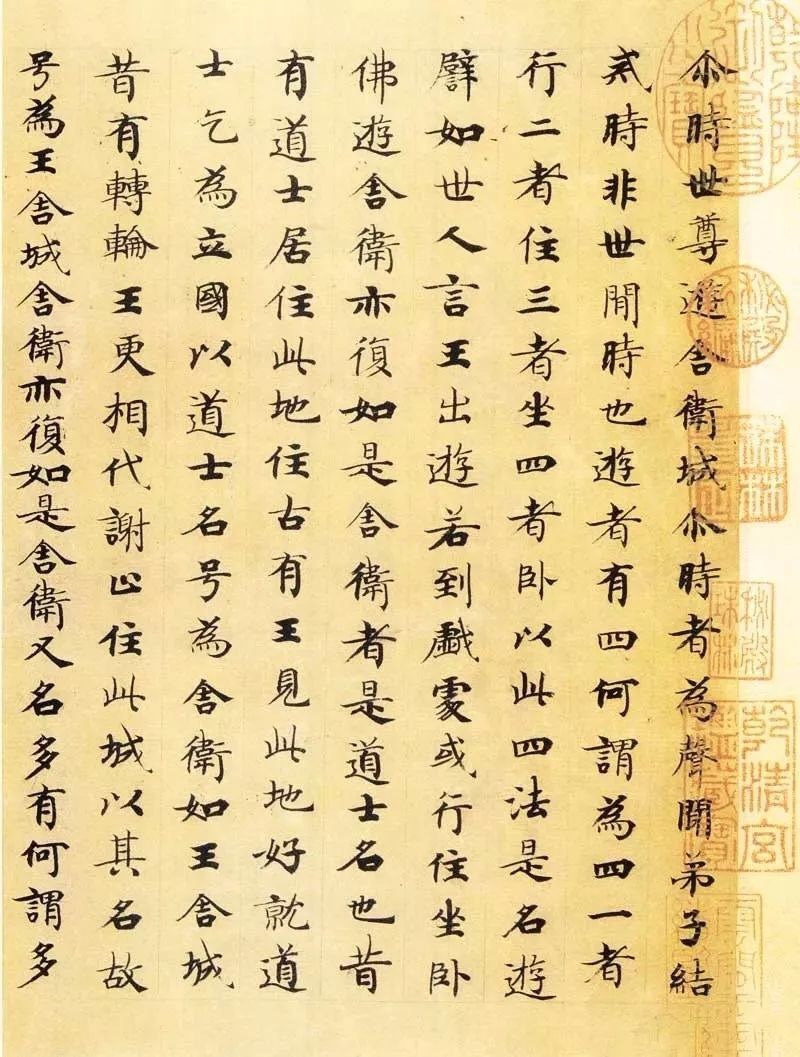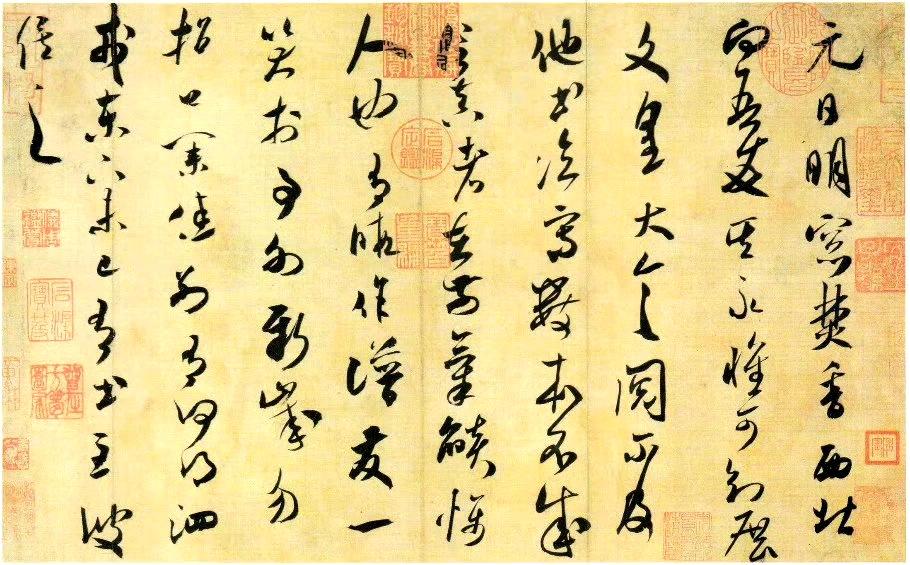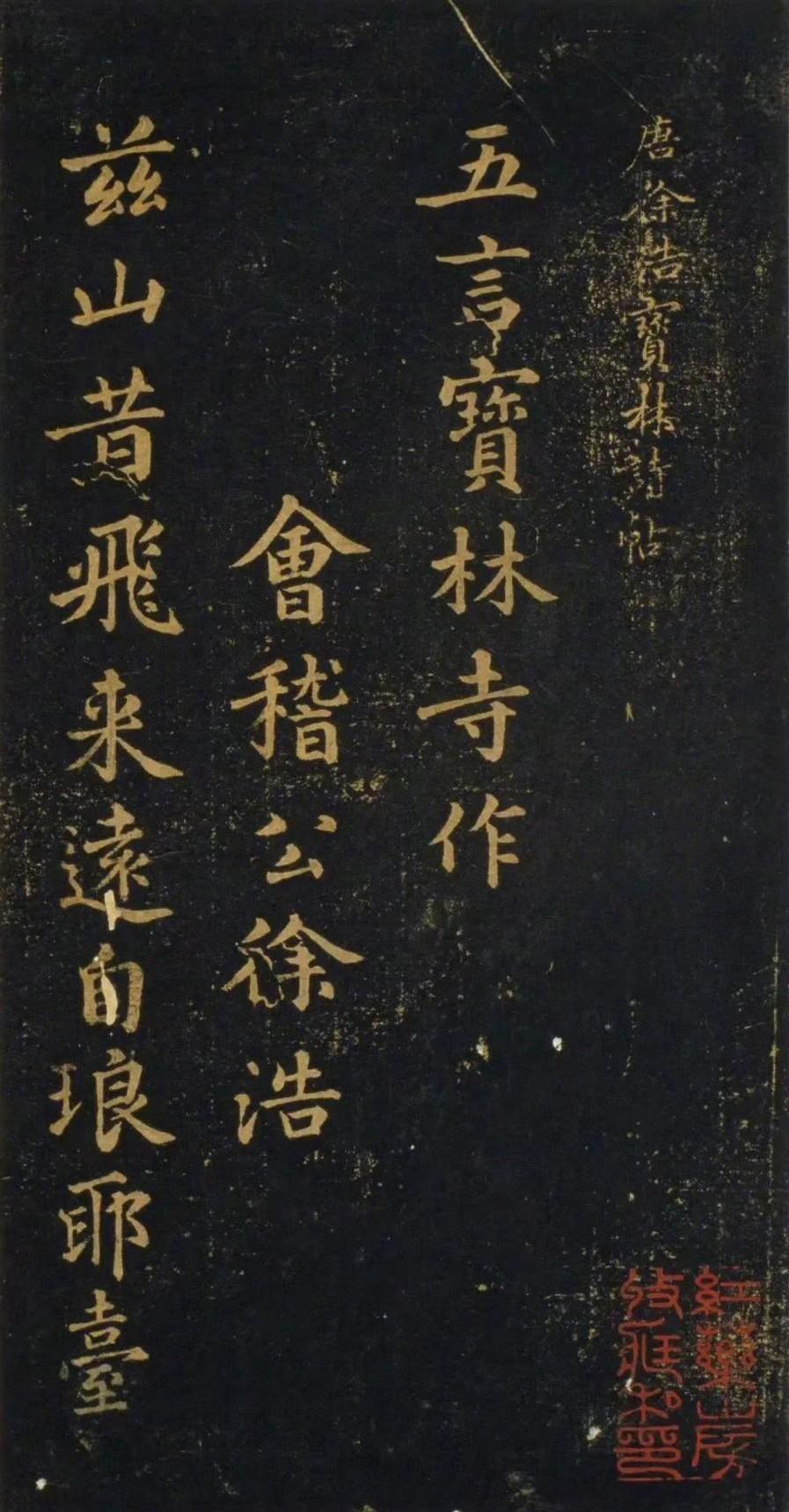1947年,48岁的华艺名家张大千,向女儿知己徐雯波追求结合。 48岁的国画大师要娶16岁的“女儿闺蜜”,这场婚事让整个上海书画圈炸开了锅。 姑母拍着桌子骂“乱伦”,原配黄凝素把自己锁进佛堂三天,可张大千手里攥着僧袍,眼里只有那个刚经历空袭、还护着他画卷的小姑娘。 张大千这辈子的感情,总跟画笔缠在一起。 20岁那年,表姐谢舜华病逝,他穿着僧袍在天童寺待了三个月,最后还是舍不得砚台还了俗。 后来娶黄凝素,也是看上她身段好,能当仕女画模特,《执扇仕女图》里的丰腴美人,原型就是刚嫁过来的她。 可等她生了八个孩子,腰身粗了,他笔下的仕女也就跟着换了模样。 就在黄凝素以为日子会这么过下去时,张心瑞带回来一个小姑娘。 徐雯波是女儿的闺蜜,常来家里玩。 那天张大千在画室画荷花,一抬头看见她站在窗边,阳光漏过发梢,他后来在日记里写“眸如秋水,竟有故人之影”。 这“故人”是谁,没人说得清,只知道从那天起,他画室里的宣纸,开始多了些清瘦灵动的轮廓。 1947年春天的空袭来得突然。 警报响时,张大千正收拾画稿,徐雯波疯了似的冲进来,把他最宝贝的那卷《长江万里图》死死抱在怀里,趴在桌子底下护着。 等警报解除,画没事,她胳膊却被桌角蹭出了血。 张大千盯着那道血痕,突然说:“我画尽天下美人,却独缺你这般有勇有谋的灵魂伴侣。”那时她已经怀了身孕,这成了谁也绕不开的坎。 姑母提着棍子找上门时,徐雯波躲在张大千身后发抖。 黄凝素穿着素衣从佛堂出来,说“你若非要娶她,我便出家”。 张大千没说话,转身从柜子里翻出那件在天童寺穿过的僧袍,往桌上一扔。 三天后,黄凝素松了口,时人记载“大千画室三日不启,终以僧袍示妻,乃定”。 婚礼上,徐雯波红着脸叫“伯伯”,被他轻轻拍着背纠正:“自此时起,称呼我大千。” 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平静。 徐雯波成了他新的模特,仕女画里的人物突然变了风格,1956年的《双美图》,仕女眼神里没了过去的娇羞,倒多了几分倔强。 有次张大千在巴西画《云山万众,寸心千里》,画到云雾缭绕处,笔突然顿了,徐雯波递过一杯热茶:“想什么呢?”他指着画说“想你护着画卷的样子”,那画后来被台北故宫收了去,成了镇馆之宝。 再后来他们去了美国,1969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办展,徐雯波跟着忙前忙后,从布展到接待,连馆长都夸“张先生有位得力助手”。 她不懂多少英文,却记得每个展品的来历,连颜料怎么调都能跟工作人员说清楚。 张大千在台上致辞时,总往她站的方向瞟,那眼神,跟当年在画室看她护着画卷时一模一样。 后来张大千在巴西画《云山万众,寸心千里》,笔锋里的牵挂藏都藏不住。 那卷当年被徐雯波护在怀里的《长江万里图》,后来成了台北故宫的藏品,而那个总在画室里帮他研墨的身影,早和他的笔触融在了一起。 把生活里的羁绊熬成创作底气,或许这才是他们这段关系最难得的地方不是谁成就了谁,而是两个人的日子,真真切切地活进了画里,成了别人拿不走的故事。